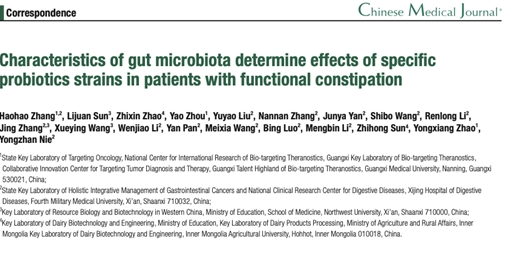而反观今日,能称得上是完全创新的药物屈指可数,我们更多看到的只是对原有药物的改进,甚至只是更名换装。不少患者担心,未来我们能否有足够的药物应对日渐复杂的疾病,新药开发走进死胡同了吗?
旧有模式风光不再
在那个制药业的黄金时代,获取成功的秘密就是两个字——砸钱。新药开发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勇敢者的游戏”,投资者往往采取大面积、大投入的方针,将巨额资金投在“重磅炸弹”级的畅销药上,希望通过后期销售所带来的大把现金抵消在研发时所产生的成本。
这一招虽然简单,却能经常奏效。世界10大制药公司在1990年时将销售额的10%用于研发,到2002年时增加到了14%。此举在为我们带来了新药的同时,也让制药行业成了当时最赚钱的行业。统计显示,即便在2002年宏观经济下滑时,财富500强名单中的10家制药公司的利润总和(359亿美元)比其他所有490家企业的利润总和(337亿美元)还要多。
但黄金时代也有其衰落之时,2002年往后不少企业发现新药的开发越来越难,旧有的“重磅炸弹”模式已不再灵光。2002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78种新药中,只有7种被FDA认为是对旧药有所改进,剩下的71种只能算是模仿性的创新药,与已上市的旧药相比,疗效不会更好。非但如此,受宏观经济影响,新药研发成本不断上升,目前一种新药从开发到上市至少需要10亿美元,所需时间可能长达15年。此外,随着旧有畅销药物专利保护期行将届满,专利困境给制药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药物专利到期后,仿制药在第一年可占据50%的市场,第二年可占据70%—80%的市场。
一些业界人士分析称,前些年药物开发的繁荣其实源于大的制药公司抢先摘下了“低挂的果实”,将最容易发现的药物变成了产品,而留下的将是那些难啃的“硬骨头”。
三大难关卡住创新
牛津大学转化医学教授蔡斯·邦特认为,这或许源于我们对人类疾病和现有药物的模式还没有足够的了解。例如,解热镇痛药扑热息痛(商品名称有百服宁、必理通、泰诺等)这种常用药,我们经常服用,却并不知道它具体是如何工作的,也不知道它作用的部位在哪里。“如果我们连这些都不知道,又如何能设计出更好、更有效的药物分子?”邦特说。
要寻找新药,首先要确定新的目标,例如某种能缓解或治愈疾病的蛋白质。但在人体中有2万多种蛋白质,每种蛋白质都可能作为发现药物的目标,各种蛋白质既相互联系又各自不同,要从中找到准确有效的药物标靶并开发成药物,几乎和中彩票一样难。
另一个问题就是重复。“出于对竞争的考虑,很多研究小组不会公布自己的失败,或者即便公布也会拖到很晚。这样一来,对同一目标进行研究的其他学者、公司或研究机构会继续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重复已被验证过的错误,直到其重演。”邦特教授说。
不过好在一切正在改变。由于新药开发的复杂程度远超以往,合作开始成为无法回避的因素。在互联网时代,开源的思想也开始被一些制药公司所采纳。2010年,葛兰素史克公司公开了13533种对疟疾有潜在治疗效果的化合物的数据,希望通过分享信息,帮助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设计出一种治疗效果更好的新药。这是制药行业首次大规模将开源开发模式应用到新药开发上,通过这种模式可能创造出一种不属于任何公司的新药。
葛兰素史克公司新药开发部主任帕特里克·瓦伦斯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必须予以打击。把这些化合物公布出来让每个人都能看到,或许是一个更好的主意。或许就有人比我们更聪明,能从中发现某些我们没有注意到地方”。“不过我们还是需要面对现实。由于存在竞争,永远都会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复。”他补充说。
即便如此,牛津大学的邦特教授表示,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已经决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会将结果及时公布。
此两点外,另一个困扰科研人员的难题便是制药业的“死亡之谷”。它起初被用来形容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的惊险过程,因为不少看上去极有希望的药物都在这个阶段折戟。随着金融危机的发展,“死亡之谷”的问题也日渐严峻和多样化,这个深谷不仅存在于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之间,同时也存在于患者利益和商业利益之间。此外,医药开发工作还必须同时面对资金短缺和大量失败的双重重压。
英国癌症研究中心的保罗·沃克曼教授认为,诸如维康信托基金这样的慈善基金或许能解决这一难题。维康信托基金会是世界最大的研究慈善机构。基金会的目的是“通过资助最优秀的头脑实现健康的突破性进展”,在资助生物医学研究的同时也支持公众对科学的认识。其年度资助预算超过美国霍华休斯医学研究所,与英国公共资助机构医学研究委员会相当。沃克曼相信,在多方努力和各种创新开发模式的帮助下,新药开发一定会走出当前的困境。
何不打开另一扇窗
沃克曼教授乐观地认为,科学仍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为我们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机遇。“科学正在引导我们从反方向寻求重磅炸弹级的新药,那就是个性化医疗。未来医生会根据患者特征和基因测试的结果来为其开出独一无二的药物。虽然就单种药物来说,受益者的数量会相对减少,但效果将远远优于那些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的畅销药物。此外,掌握大量患者信息,从患者角度进行研发,更有效接近患者,也将成为制药企业的新策略”。
传统药物开发模式中,相对于临床试验的高额开支,实验室中科研人员的耗费可谓小巫见大巫。新药的高额研发成本主要来自于临床试验的高失败率。而在个性化医疗时代,这一切将完全改观。根据少量患者特点设计的药物或治疗策略,规模更小,时间更短,成功率更高,相应的费用也会随之降低。这让新药开发的经济成本重新得到了平衡,“死亡之谷”也将变得更易跨越。
沃克曼曾预言,通过这种方式,抗癌新药早期临床研究的成功率有望在5年内从现在的5%上升至50%。
不久前这一预言已经得到了验证。2011年8月17日,FDA批准Zelboraf(vemurafenib威罗菲尼片)用以治疗晚期或不可切除的黑色素瘤。2012年2月20日,该药也在欧盟获批。罗氏公司开发此药从一期临床试验到2011年发布总共还不到5年,人们似乎又重新找到了那久违的速度。
当一扇门被关闭时,寻找另一扇打开的窗或许是更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