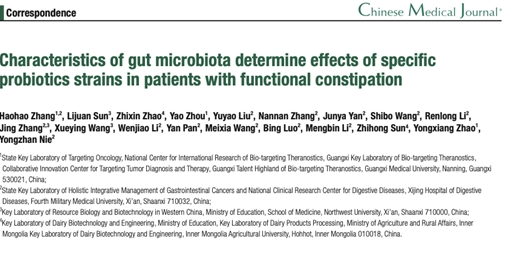一名身患霍夫曼肌肉萎缩症的俄罗斯男子欲将自己的“头”交给一名意大利临床医生,以移植一个健康的身体,进行世界上首起“换头术”。
手术对象: “害怕吗?当然”
在接受英国媒体的独家采访时,来自俄罗斯、现年30岁的计算机科学家瓦雷里·斯皮尔多诺夫承认,自己就是意大利神经学家赛吉尔·卡纳维罗全球首例头部移植手术的对象,他希望手术能在明年完成。
斯皮尔多诺夫表示,他对卡纳维罗非常有信心,他说,“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不会再更改。”据悉,斯皮尔多诺夫从小罹患先天性肌肉萎缩症,每年身体情况都在恶化,现在更是只能依靠轮椅行动。因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他同意接受卡纳维罗的头部移植手术,即将斯皮尔多诺夫的头部移植到捐赠者健康的身体上,据称捐赠者将是一位脑死亡的病人。
“我害怕吗?当然,”斯皮尔多诺夫对记者说,“但是必须知道的是,我没有太多的选择,如果我不努力地试一试,我的人生也许就这么完了。”他还表示,自己经常和卡纳维罗通过电邮及网上视频通话联络,但从未见过面,医生也未读过他的医疗记录。
卡纳维罗说他收到很多人发来的邮件和信件,希望参与手术,但他还是坚持把第一个手术机会让给肌肉萎缩症的患者。他将这一计划命名为“天堂”(HEAVEN),是“头部接合手术”的缩写。卡纳维罗曾在今年年初称,人脑移植在脊髓融合、防止免疫系统排斥反应等瓶颈可被攻克,将最早在2017年实现。
换头医生: 高调宣传引争议
卡纳维罗是意大利都灵高级神经协调组的临床医生,因高调宣传“换脑”想法而引发医学界争议。
今年2月,他在《国际外科神经学》期刊刊登了一篇综述目前脑移植技术的文章,称现在技术已可以实现“换头”。他对媒体表示,将在今年6月美国马里兰举行的美国神经和矫形外科医师学会年会上展示自己的项目。
与卡纳维罗有着合作关系的哈尔滨医科大第二附属医院手显微外科中心主任任晓平说,今年6月马里兰举行的大会是世界最重要的脑外科大会,大会议程邀请卡纳维罗做主旨发言,卡纳维罗也邀请任晓平参与。
“技术层面,应该说脑移植是可以实现的。”任晓平说。他介绍,器官移植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始终在进步,但手、头这样的复合组织的移植始终没有进展,因为免疫系统的排斥性非常强,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他当时在美国的研究团队研制了新型的免疫药,能够成功控制免疫系统排斥反应,成功实现世界上第一例手移植手术,患者存活十多年。
但头部依然是全身最特殊的地方,头部移植的最大两个挑战,除了因复合组织而产生的免疫系统排斥反应之外,另一个就是中枢神经系统的连接。
人脑与脊髓连接,组成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是整个神经系统的控制中心。和人体其他一些神经不同,中枢神经一旦被切断,将不会生长,其功能得不到恢复。
对于这一问题,卡纳维罗自信地解释,受体和供体两者的脊髓末端可以像两束意大利面一样绞起来,他将使用一种名为聚乙二醇的化学物质冲洗融合的区域,并持续注入好几个小时,最终,这种化学物质可以像胶水让两端脊髓融合,就像冲过热水后,两段干的意大利面黏在一起一样。此外,还可以采用注入能够自我更新的干细胞的方法让脑髓跟脊髓连接。卡纳维罗表示,手术对象在术后的昏迷情况将可能会持续四个星期,而在这一过程中,医生会用电极刺激手术对象,进而加强与新神经的连接。如果手术对象体内出现排斥情况,医生则会向其体内注射抗排斥免疫抑制剂。卡纳维罗说,如果手术成功,那么结合物理疗法,病人可在一年之内恢复行走能力。
质疑者众: “会比死更难受”
在任晓平看来,卡纳维罗能够去挑战现代医学的“终极挑战”,有着很大勇气,他说,如果能做成人脑移植的第一例,也意味着现代医学的重大突破。
他表示,虽然这项手术在理论技术上可以实现,但因缺乏客观的实验室数据,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脑部移植到目前为止也只有小鼠实验,即使是他们所做的小鼠实验,也只进行了短期的观察,没有长期的观察,而到现在,也尚未有做猪、猴等更高级动物的实验。
“免疫系统的排斥性反应还是要长期观察才能出现的,术后不会很快出现。”他说,“中枢神经的恢复,也很有可能使得病人瘫痪。”
任晓平认为,当前做脑部移植,手术当时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术后恢复意识及智力应该没问题,但恢复身体感觉和运动功能不确定”,这也就是由于中枢神经功能未能或有可能即将突破的挑战。
据悉,头部移植手术非常复杂,估计需36小时才能完成,成本达75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7000万元),由于该手术涵盖很多史无前例的难题,因此这个计划遭到了医学界、伦理界和不少媒体的强烈反对。更有批评者说卡纳维罗的计划是“纯粹的幻想”。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临床神经外科教授哈利·戈德史密斯曾经完成过使脊髓损伤病人恢复行走的手术,他对此表示,“这个项目太匪夷所思了,手术中存在太多的并发症,我不相信它真的能成功。试图让一个人在昏迷中保持健康达四个星期之久,这根本不可能发生。”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协会的巴特·杰尔医生则认为手术后果严重,甚至“会比死更难受”。
卡纳维罗则对头部移植手术保持冷静,“如果社会不希望这项技术,我也不会勉强。但是如果只是美国或欧洲不希望手术发生,并不意味着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不需要。我会努力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揭秘手术过程
1 医生首先会冷冻病人和捐赠者的身体。
2 用超锋利的手术刀片同时将两人的头颅从脊髓割下。
3 再用卡纳维罗口中的“魔术材料”聚乙二醇接驳病人头颅和捐赠者的身体。
4 最后用手术针线缝合肌肉和血管。
换头手术靠谱吗?
俄罗斯曾成功开展动物实验
其实,历史上,俄罗斯就曾成功开展动物实验。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主任医师、教授朱宏伟介绍,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进行了狗的“全头移植”手术,引起了全球的轰动。手术估计至少进行了1000次才获得成功。被激怒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咽不下这口气,于是,美苏正式开始了“换头战”。
两年后,美国科学家成功地进行了“动物异种换头”:把一只小狗的脑袋“搬”到一只猴子脖子上。可是,仅仅过了6个月,苏联科学院一位生物学教授进行了一次难度更大的异种移头——将一只小白猫的头“装”到一只灰兔身上。更重要的是,“装配”成的新动物完全不像上述两只“换头动物”那样呆头呆脑,它不仅活泼好动,逗人喜爱,而且别有一番情趣。
而意大利神经学家赛吉尔·卡纳韦罗计划实施的人体换头术也或许并不是首例。俄罗斯人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展了世界首例人体换头术。据说是1985年基辅市的一家医学研究所成功将一名米叫克哈尔的晚期骨癌患者的头脑移植到一个刚刚被处决的罪犯的身躯上,手术大获成功。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手术前未能发现罪犯患有心脏病,移植后第二年,米氏便突发心脏病,最后死于心血管系统的并发症。“虽然患者存活时间并不长,但现在看来,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手术算是低水平的成功。”但该事情发生于美苏冷战时期,但真实性至今没有得到权威媒体的证实。
如果“头部移植”手术能获得成功,那将给患有绝症的病人提供出路。换头,听起来就很恐怖,不少业内人士都对这个手术持怀疑态度。据了解,这一移植手术需要100名外科医生持续进行36个小时,费用高达750万英镑。
技术层面基本可行
对于换头手术究竟是否可行,任晓平表示,与其他器官不同,人脑相对特殊,开展换头手术主要面临中枢神经再生、免疫排斥反应、伦理学等挑战。
朱宏伟告诉记者,目前这一手术在技术层面基本是可行的,一方面,现在其他器官移植开展较多,这也为脑部移植积累了很多“经验”。有些器官移植手术已经比较成熟,如肝脏移植。像肺移植、心肺联合移植等,国内外都开展了很多,手术面临的排异情况与脑部移植是类似的。另一方面,免疫抑制类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提升也为脑部移植的开展提供了保障。
虽然曾成功进行手移植手术,任晓平仍担心,手部移植手术成功解决了排异反应的问题,但作为一个特殊的复合组织,人脑包含中枢神经,现有免疫方案能否控制脑部排异反应,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适合少数极端情况
在任晓平看来,如果这一手术能够开展,也主要适用于少数极端情况。除了像瓦雷里·多诺夫这样的先天性肌肉萎缩患者(脑部发育正常,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渐萎缩,后期甚至呼吸困难)之外,严重外伤患者,尤其是高位截瘫患者及部分癌症患者、因其他疾病导致多脏器衰竭的患者也适宜开展,“尤其是部分癌症患者,病情可能在经放化疗等治疗后发生转移,如果未发生脑部转移,换头手术也是挽救生命的一种方法。”
挑战
脊髓连接后或致部分功能丧失
尽管如此,从技术层面看,换头术仍面临几个技术难题。朱宏伟介绍,头颈的顺利连接是其中之一,骨骼、血管及肌肉的连接目前不存在技术问题,关键在于脊髓的连接,现在能够部分实现,即结合后可能会丧失某些功能,这也是换头手术最具挑战性的地方之一。如何保证连接后肢体的运动、感觉、反射功能良好,这也是患者生活质量提高的根本。近年来通过膜融合剂和电刺激等技术诱导脊髓与脑神经传导束生长连接,人机接口技术的大幅进步,已经可以使部分截瘫患者站立行走,可以通过此渠道实现移植后的功能重建。
中枢神经可否再生
中枢神经的连接是换头手术的另一个技术难题,“以前我们认为中枢神经不可再生,但近五年的研究发现,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同样可以找到神经干细胞,这也证明中枢神经存在修复的可能。”朱宏伟介绍。
在任晓平看来,借助干细胞、电刺激、生物活性因子等手段,中枢神经有再生的可能,但目前还没有取得最终的突破。
“换头术的失败率会比较高。”朱宏伟指出,换头手术与组织配型类似,血型、白细胞抗原相似度高,存活率相对更高,如果两者匹配度不高,手术成功率也会受影响。
伦理讨论:换了头,他究竟是谁?
如果换头手术得以开展,随之而来的伦理问题不可回避。朱宏伟表示,在国内外,伦理问题都是换头手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这关系到术后的这个人究竟是谁。“A的脑子与B的躯体相结合,作为一个社会人,传统观点认为意识由脑产生,躯体提供了支撑平台。但近二十年中,医学研究发现,躯体分泌的激素同样会影响人的表达、情感等意识内容,我们究竟该怎样界定接受换头手术的患者?”如何建立伦理学上的秩序,这也是很有挑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