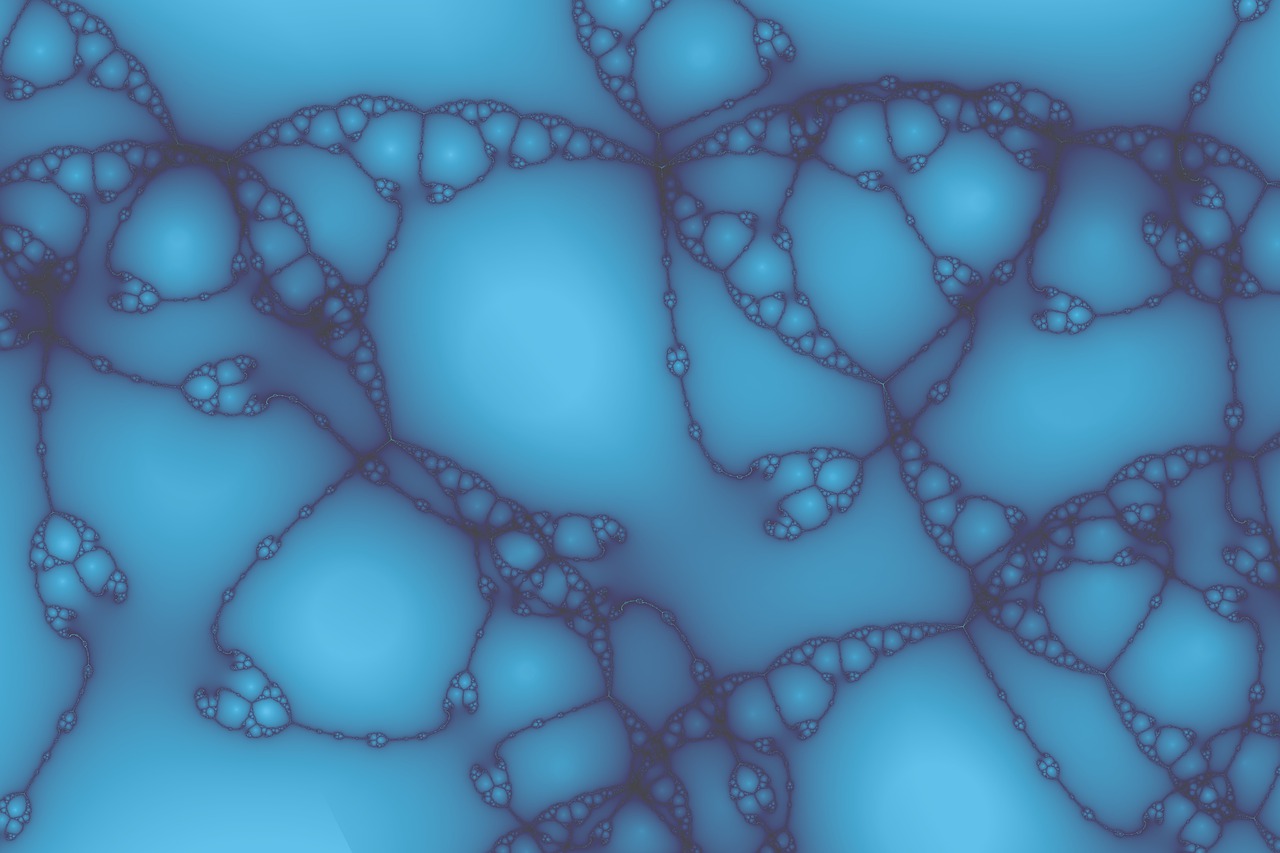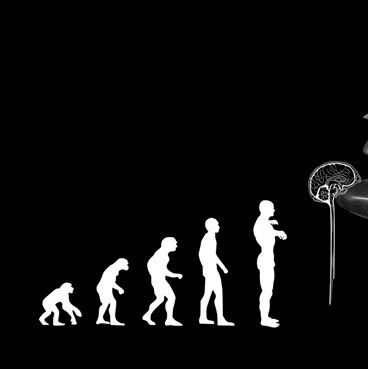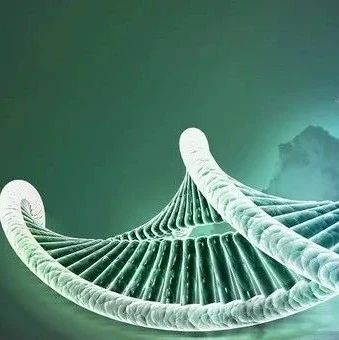如果遗传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家长们对子女的遗传情况了解得更多,知道孩子们从自己这里遗传到了什么,而且家长可以据此采取某些行动,那样可能还会带来不可预料的结果。(图)
20年前,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刚刚启动之际,我们就已经知道有几十个基因如果出现了问题就会导致遗传性疾病(mendelian diseases)发生。这些比较少见的疾病通常都是因为某一个基因发生突变而导致的,而且这些突变基因根据遗传法则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今天,科学家们已经为大约3000个这类致病基因进行了作图分析。随着基因筛查技术的越来越先进,一部分有先见之明的人可能会在准备怀孕之前或者是选择伴侣之前就先去做一个检查,看看自己或者对方是否携带了致病突变基因。选择体外受精方式的家长们也可以对胚胎或者胎儿进行筛查。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手段,利用母亲的血样就能够对其中含有的胎儿DNA片段进行测序,进而获得完整的胎儿DNA序列。
基因筛查工作远不止于此。以前我们一直都认为,如果想通过遗传筛查的方法预测出人体患上癫痫或II型糖尿病这些常见疾病的风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类疾病的遗传背景都太过复杂,可是这一观点被彻底推翻了。最近有研究发现,有一些在普通人群中比较少见的遗传突变对于人体是否会患上这些常见疾病,会患上哪些疾病,什么时候患病,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在5年之内,我们将对数十万人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届时将有可能发现更多的遗传突变位点,其中有一些突变可能单独就能用于疾病预测工作,有一些可能结合起来也能用于疾病预测工作。
可是社会和政府部门很明显还没有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好准备。我们现在应该开始考虑下面这些问题了,在解密子女基因组的问题上有没有一个限度,限度在哪里?这样做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是什么?在了解了遗传危险之后,该由谁来决定是否应该采取某些行动,是政府还是个人?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生物学家们就形成了共识,绝大部分常见疾病的遗传基础与孟德尔式遗传疾病有着本质的区别。很多人认为这些疾病(除开少数几种因为基因出现非常严重的突变而导致的致病)是多种常见突变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常见是指在人群中出现的比例超过1%或5%。这些突变中每一种突变对人体患病的影响作用可能非常小,或者作用不固定,比如在某些环境下对人体有害,但是在某些环境下可能还会对人体有利。这样看起来遗传学筛查似乎没有太大的用处。虽然这种遗传筛查可能有助于发现泰萨二氏病(Tay-Sachs disease)和囊性纤维化病(cystic fibrosis)这样的孟德尔式遗传疾病,但是对于“复杂的”常见疾病似乎没有什么帮助。
不过,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些对多个已知突变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表明,这些突变基因中绝大多数都与其它的突变基因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标准化了的群体进行研究,遗传学家们可以了解到人体基因组内所有这些突变基因的真实情况。有一些科研小组对数万个基因组进行过研究,最近甚至有人对数十万的基因组进行了研究。可是对于绝大多数的疾病来说,我们只能认识到它们背后遗传机制当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另外,即便遗传学家们发现了很多突变基因,但是由于每一个基因的作用都很弱,所以我们也很难知道哪一个突变基因才是最主要的致病基因。
另外一个可以证明多个常见突变决定一个常见疾病的例子就是基因拷贝数变异。这种突变要比孟德尔式遗传疾病更加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在这两种情况下突变都有明显的致病作用,对个体的患病风险也都有非常大的决定作用。我们已经发现了好几种可用于预测常见疾病,比如自闭症和癫痫等疾病患病风险的拷贝数突变因素,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迅速增加。
换句话说,至少有一些常见疾病可能是由多个非常罕见的突变共同导致的,不过这些突变每一个的作用都非常小,而且对每一个人的作用还都不一样。
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医学遗传学领域里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常见突变是导致常见疾病发生的主要因素。不过,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个观点在这四年来也获得了很多证据的支持,那就是很多常见疾病也会受到很多影响巨大的罕见突变施加的强大影响。
这一发现给研究人员带来的最大麻烦就是他们不得不筛查更多的遗传因子,每当多发现一个这种强力作用因子,就得扩大一次搜索范围。
在对孟德尔式遗传疾病开展的研究当中获得的最大收获就是让我们认清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是发现了致病因素,我们也不可能很快找到有效的治病方案。不过也有成功的案例,比如因为缺乏葡萄糖脑苷脂酶而使患儿出现贫血、骨痛和骨质缺损的高雪氏症(Gaucher’s disease)患者在注射人工合成的葡萄糖脑苷脂酶之后,症状会得到极大的缓解。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在发现了致病机制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仍旧不能彻底地治愈该疾病。在面对有些疾病,比如囊性纤维化症时,我们可以通过恰当的护理和治疗缓解患者的症状,延长他们的生命,但是这不叫治愈,而且我们到今天也没找到这些疾病的致病基因。
同样,为非孟德尔式遗传疾病找到治疗方案也是十分困难。与此同时,由于基因组测序费用不断下降(今天进行一次基因组测序只需要4000~5000美元,这和一些被广泛使用的影像检查的费用已经差不多了),家长们对于通过遗传筛查帮助他们避免孕育出缺陷后代的需求却在与日俱增。
现在,学界对于在遗传学筛查工作中究竟应该检查哪些项目(突变基因)还没有达成共识。目前在美国和欧洲主要针对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发病时间较早的严重疾病,比如泰萨二氏病、唐氏综合症以及囊性纤维化病这类疾病的致病基因进行筛查。实际上,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产前(包括受孕前、胚胎植入前或孕期)遗传筛查工作以来,在美国新生儿中泰萨二氏病的发病率已经降低了90%。在美国有一些生殖中心里甚至还会对亨廷顿氏病这类发病时间较晚的遗传性疾病进行产前筛查。不过目前还没有人对APOE4基因进行筛查,有证据表明该基因如果发生突变,人体患上早老性痴呆病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还有一些基因如果发生突变并不一定会导致疾病发生,又或者这些突变基因只是与成年之后或老年时罹患的疾病有关,因此对这类突变基因的筛查工作就显得不是那么急迫,它们的重要性当然不如会导致幼儿死亡的突变基因那么重要。不过,有一些APOE4等位基因携带者也非常想知道他们的突变基因是否会遗传给子女。
现如今,在产前遗传筛查工作中究竟应该检查哪些基因似乎正在变得是由政府组织说了算,比如英国人工授精与胚胎学管理局(UK 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Authority)和美国的临床受精医学中心(medical practitioners in fertility clinics)一类的机构。德国议会正在考虑允许某些机构进行产前遗传学检查,以免出现流产或死产。不过原文作者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让父母本人来选择是否将APOE4基因这类与患病风险高度相关的突变基因遗传给子女,尽管这样做会面临更多的问题,比如这个选择的度如何把握等。
艰难的抉择
在几年之内,我们一定会发现更多的致病突变基因或者潜在致病突变基因,再加上数不胜数的、功能未知(不知道是否会致病)的突变基因,这一切一定会让我们猝不及防,从而感到束手无策。比如如果一对父母想要借助体外受精技术避免他们的子女携带五种突变基因,那么医生首先就应该对体外受精的胚胎进行遗传学筛查,找出里面最有可能是健康的那一个。否则,这对父母就应该终止妊娠,以免生出不健康的宝宝。
不过这一切都很难真正得到实施。今天,科学家们已经习惯于对某些细胞里的DNA序列进行有目的的“修补”工作。虽然他们还不能够对人体生殖细胞(精子细胞和卵子细胞)“下手”,但是有好几项有望用于对生殖细胞DNA进行编辑工作的技术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这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有一种从本质意义上完全不同的遗传学筛查。
相比常见的基因突变,少见的突变对于基因的“伤害”更大。我们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人类基因组变异中心(Center for Human Genome Variation at Duke University)里收集的各种全基因组测序数据里发现,每一个人体内都携带有数百个独一无二的能够使基因编码蛋白发生改变的基因突变,这些突变在人群中出现的比例都不到1%。如果有可能的话,是不是有父母会出于让后代安全的目的而选择不让这些突变遗传给自己的子女呢?
进行产前遗传学筛查可能会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各种各样的遗传风险因子可能会造成各种不同的,甚至是不可预知的结果,它们有时可能会致病,但有时却又不会给人体造成伤害,甚至有可能会赋予人体某些比较不错的能力。即便是在最简单的孟德尔式疾病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有超过30%的突变在之前被认为是对人体有害的,可结果却发现它们根本就是无害的。如果大批量的“消灭”各种与疾病有关的突变基因,那样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比如增加人体对某种感染性疾病的易感性,又或者有可能会扼杀掉人类的创造力等等。
对于究竟应该检测哪些突变基因,以及检测的限度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现在是时候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