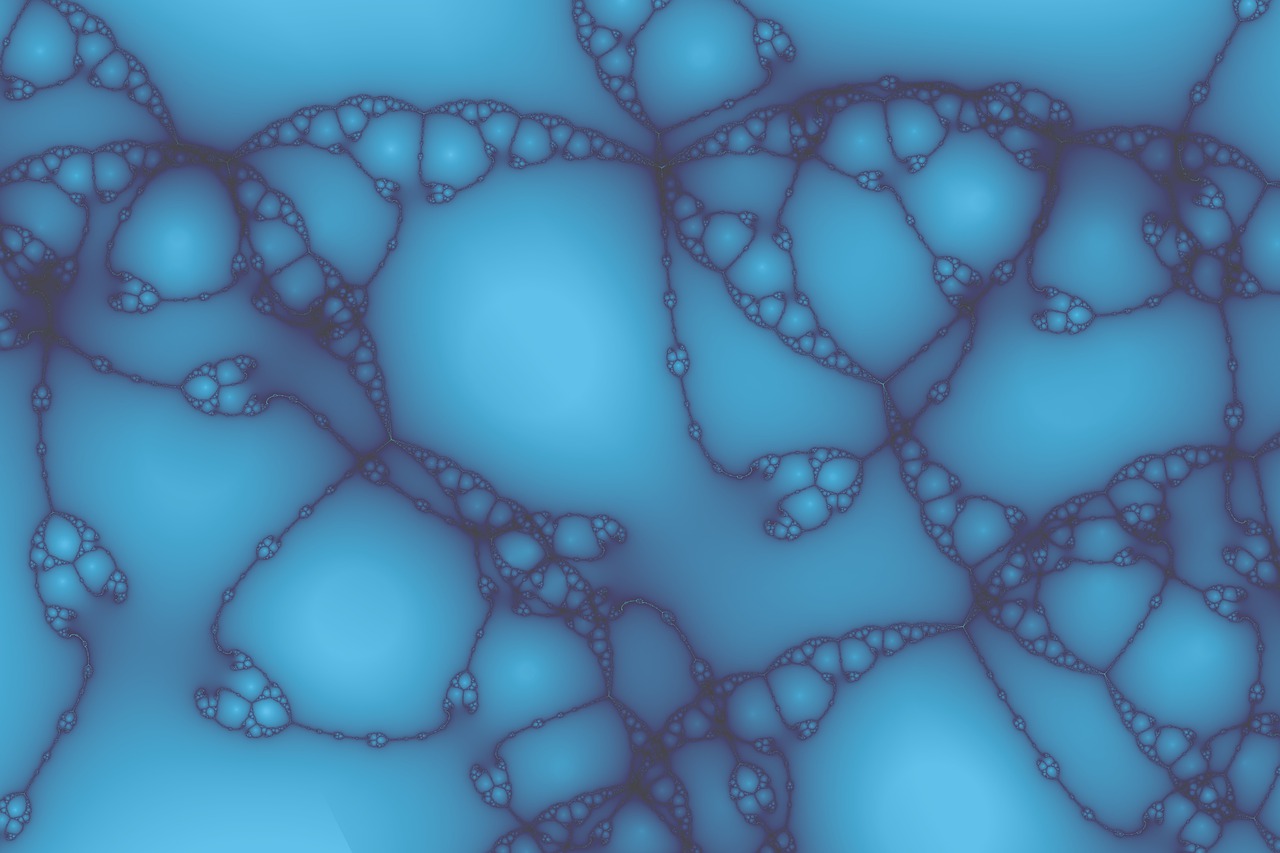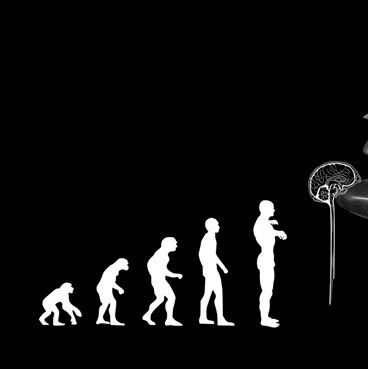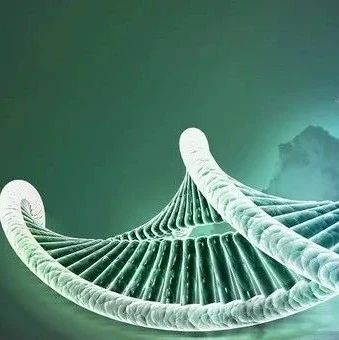纪念扎西德勒
西藏一行,荡起心中扬尘一般的感慨。本以为会有一大堆的话要写,关于虔诚,关于朝圣,关于那个能在瞬间荡涤所有仇怨疲惫的纳木错。但一去一回都是急匆匆,直到今晨被闹钟吵醒,然后闷死闹钟继续睡。
再醒来时,是被同屋的吕兄叫醒的。已然9点多,上班迟到已成定局。依稀记得今天早上还有个会议要参加。于是匆忙洗刷一下,登上布鞋,胡子拉碴就往办公室奔去。走到办公室,放下包,抄起本子和笔就冲向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是几个不认识的人在开会。回到办公室自己座位上在Am给杨头问了下才知道,领导们都不在,上午会议取消。俺滴个亲娘二舅奶奶,紧绷的心弦一下子松了很多。
从去西藏到现在,神经都是绷得很紧。连续很多个晚上加班熬夜熬到两三点,尤其是在高原上,越是紧张越感觉氧气不够用。完全有一种蚂蚁撼大树的力不从心。有时候便突然地很绝望无助。就像一个刚刚会站着的孩子摔倒在地上,哇哇地哭,任凭你大声的哭,还是没有一个胳膊把你扶起来。于是哭完了,抿抿嘴,连眼泪都不擦就自己努力爬起来,自己学着走路。
在西藏的日子,心情如同山路一样颠簸着,极喜悦,极悲伤,极虔诚,极叛逆。在见到纳木错的时候,所有的高原反应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近乎欢呼雀跃在湖边奔跑着,举着电池电量殆尽的相机抓取着每一个风景。当无意中几个安详的藏家老人和小朋友出现在相机里,他们似乎早有准备地走过来,伸着手喊着:“一块,一块,拍照一块”。这几个娃娃那清澈的眸子里面似乎只有这几个字“一块,一块”。在心中,一切的神圣,一切的淳朴被一下子颠覆性地毁灭。当时,我怀着凌乱的心情,掏出一大把零钞,竟然还笑着把钱塞到他们手里。当时究竟是个怎样的心情,也许只有身边的纳木错和云后的念青唐古拉山能知晓。
我不想评论太多,记得在当时我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我说没有信仰的人们都是垃圾,这些人带去的物质污染了当地的环境,这些人带去的思想污染了当地的心灵。佛法无边,却依旧感化不了世间执拗的心灵。我想,末法时代,纵是最圣洁的高原也是难逃此劫。既然是冥冥中早已注定,我又再能有何感慨?佛说,法在尘世间。
去大昭寺,不知道那天是当地的什么节日,密密麻麻的人群绕着大昭寺做顺时针朝拜。我提议了一下,便和同行的其他两个兄弟一起随人潮顺时针走动。朝拜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穿着藏袍,有的穿着时尚。穿着、年龄、性别都不同,但脸上表情刻写着一样的凝重,一样的虔诚。有人曾小声说了句,这里千万别发生暴动。我说在这个遍地虔诚的时刻是没有暴动的容身之处的。但回去的路上,我给自己的话加了一个限定条件:前提是,你和他们的思想、行为合拍。
看了很多眼的念青唐古拉山,后来发现那白云极像是挂在山峰脖子上的哈达。懵懵懂懂似乎对哈达的来源有了一个浅浅的认识。算下来,在西藏总共接受了7条哈达。其中有3条是吃饭时候由身为服务员的藏家姑娘给挂在脖子上的。在当时,又是献歌,又是敬酒的,确实颇有感觉。接下哈达,念一声扎西德勒,借着酒意有种把心交给高原的冲动。后来,有个兄弟给了句实在话,他说那些哈达是花钱买来的。你不给钱,人家才不会给你献哈达。这句话倒又让我心里颠簸了一番。钱,似乎很伟大,什么都能买得到。但钱,又似乎什么都买不到。其实,钱就是一个工具,有罪过的,是人的贪念。扎西德勒据说是万事如意的意思,但愿不是随心所欲或者为所欲为。
从西藏回来,便一直在加班。所长见了我,也给我施压。于是心头无形中多了一副担子,那是作为男人的担子。无论多沉,无论多累,选择了扛着,就要扛起来。只要有一口气在,便要努力扛。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有寸步难行的感觉。困倦,甚至饥饿,在漫长的午夜竟然还滋生了许多的绝望。我走到杨哥的办公室,屋里面烟雾缭绕。香烟,或许是男人的味道,但我感觉我并不需要那些香烟来衬托。
最后终于把稿子交上了。对自己笑笑。小子,这世上,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
2011-6-21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