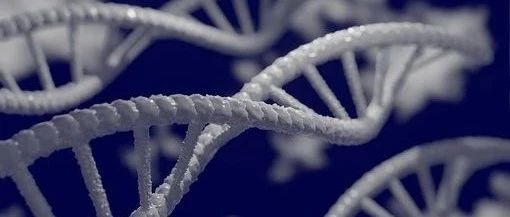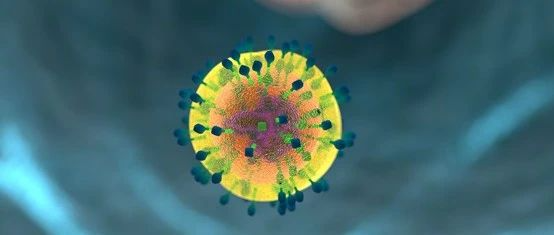If we have made such exponential progress in combatting HIV, why haven't our perceptions of those with the virus evolved alongside? Why does HIV elicit this reaction from us when it's so easily managed? When did the stigmatization even occur, and why hasn't it subsided?
演讲实录
在这场演说的一开始,我想让各位看一张照片,在座很多人可能已经看过这张照片。我想请各位花一点点时间,看看这张照片,然后好好深思出现在脑海中的东西,那些东西、那些话语,是什么?现在,我想请各位看着我。当你们看着我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把我和上面那个人区隔开的是什么?

照片中的男子名叫戴维柯比,照片是在1990年拍摄的,他因为艾滋相关的疾病病危,后来照片在《生活》杂志刊登出来。真正把我和柯比区隔开来的东西,只有一样,就是在治疗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方面,约三十年的医疗进步。
所以,接着我想要问:如果在对抗艾滋病毒上我们已经有这么快速的进展,为什么我们对于艾滋病人的感受没有一并演进?既然艾滋病病毒已能被简单处理,为什么它还会引发这样的反应?这种污名化是何时发生的?为什么它还没有消失?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它们都牵涉到许多不同的因素和想法。强大的影像,像是柯比这张照片,这些是在80、90年代艾滋危机时的脸孔,在那危机的时代,非常明显会影响到已经被污名化的族群,也就是同性恋族群。所以,一般的异性恋大众看到的,是这件非常糟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已经处在社会边缘的族群身上。当时的媒体几乎就把两者──艾滋病和同性恋──当作可互换使用的词,在198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位发言人开玩笑说同性恋(GAY)代表「GotAidsYet(得艾滋没)?」那就是当时的心态。
但随着我们更了解这种病毒,更了解它如何传染,我们发现,风险的范围扩大了。1985年的莱恩怀特案例非常知名,他是位十三岁的血友病患者,因为用感染的血液治疗,让他染上了艾滋病毒,造成美国人对艾滋病毒的感受产生最深刻转变。这病毒不只出现于社会的黑暗角落,不只是同志和吸毒者才会得到,它也会影响到那些被社会视为值得同情的人,孩子们。
但那具穿透力的恐惧和感受仍然徘徊不去。接下来的几个问题,要请各位举手表示。
在座有哪些人知道,透过治疗,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不只是能完全抵御艾滋病,他们还能回到完整、正常的生活?你们都是受过教育的。
在座有哪些人知道,透过治疗,感染艾滋病毒的人能够达到一种检测不到的状态,且会让他们几乎是没有传染力的?少了很多人。在座有哪些人知道,有暴露前和暴露后治疗,可以将传染的风险减少掉至少90%?
看吧,我们在对抗艾滋病毒上有这些不可思议的进步,但这些进步却没能够影响到大部份美国人对于该病毒以及病患的感受。我并不希望你们认为我刻意轻描淡写这种病毒的危险性,我并不是不知道在艾滋病流行时的那段悲惨历史。我想传达的讯息是,受感染的人是有希望的,且艾滋病毒不再像80年代时代表着死刑了。

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我自己在一开始就问了:故事在哪里?带着艾滋病毒过日子的人在哪里?他们为什么没声音?我要如何相信这些成功经验或是这些统计数据,如果我没亲眼看见成功?对我来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恐惧→污名→羞耻:这些因素让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可以说是躲在柜子里面。我们在性方面的过去经验和我们的病例一样是很个人的信息,当你把两者部份重叠时,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空间中。当我们诚实的时候,会害怕别人对我们的感受,因此让我们在人生中有许多事都不敢去做,对于艾滋病毒检测阳性的人而言就是如此。我们要为透明所付出的代价,就是面对社会的严密检视和奚落,为什么要当烈士,如果你装成没有艾滋病的人就能有效地混过去?毕竟,没有任何身体上的特征代表你得了艾滋病毒。你身上没有戴着标牌。同化能够带来安全感,不被看见能够带来安全感。我来这里是要把面纱揭开,分享我的故事。
2014年秋天,我是大二学生,我和大部份大学生一样性活跃,我通常都会做预防措施把性带来的风险减到最小。我说「通常」,因为我并非总是那么小心。只要一次失误,我们就可能完蛋了,而我的失误十分明显。我曾做过没有保护措施的性交,而我不以为意。把时间快转三周,感觉就像我被一群牛羚踩踏过去。我过去和之后都没有体验过这种程度的身体疼痛。我会不断发烧又发冷。我会因为眩晕呕吐,很难行走。身为生物学系的学生,我比别人早接触到疾病知识,而身为一个有见识的同性恋,我对艾滋病毒有些认识,所以,对我来说,这似乎就是血清转化现象,或被称为急性艾滋病毒感染。而这是身体的反应,产生艾滋病毒抗原的抗体。很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并非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生病阶段,而我很幸运是有经历的人之一。说幸运,是因为有这些身体征兆,才让我知道,嘿,好像有什么不对劲,让我能在很早期就侦测出病毒。
所以,为了澄清,为了要能准确知道,我在校园里做了检测。他们说,隔天早上会打电话给我告诉结果,他们打来了,但他们是叫我过去,和医生直接谈。而我从她身上得到的反应和我预期的不同。她向我保证我已经知道的事,这并不是判死刑,她甚至愿意让我和她哥哥联络,她哥哥从90年代初就一直和艾滋病毒共存。我拒绝了她的好意,但我深受感动。我本来预期会被谴责的。我本来预期会有怜悯和失望,我得到的却是同情和人情温暖,我永远感激那第一次的交流。
不难想象,接下来几周,我的身体状况糟透了,情绪上、心理上,我都还可以。对这件事我很难接受。但我的身体受尽蹂躏,和我亲近的人,他们不会没察觉。所以,我请室友们坐下,我让他们知道我被诊断出了艾滋病毒,我很快就要接受治疗,我不希望他们担心。我还记得他们脸上的神情。坐在沙发上,他们抱着彼此哭泣,而我在安慰他们。因为我的坏消息,我还要安慰他们,但看到他们在乎,让我觉得很窝心。但从那晚之后,我就注意到,我在家中被对待的方式有所转变。我的室友不会碰任何我的东西,他们也不吃我煮的任何东西。在南路易斯安那州,我们都知道你不会拒绝食物的。
而我是个超棒的厨师,所以别以为我没注意到。
但从这些最初的沉默暗示之后,他们的反感渐渐变明显了,且更冒犯我了。我被要求牙刷不能放在浴室,我被要求不能和他们共享毛巾,我甚至被要求洗衣服时设定的水温要更高。各位,这不是头虱。这不是疥疮。这是艾滋病毒。它的传染途径有血液、性体液,如精子或阴道分泌液,还有母乳。既然我没和我的室友上床,我也没有喂他们母乳,
且我们又没有在重演《暮光之城》(译注:吸血鬼电影),我对他们而言是没风险的。我让他们知道这件事,但这种不舒服感仍然持续着,直到最后我被要求搬出去。我会被要求搬出去,是因为其中一名室友和她的父母谈了我的状况。她把我的个人医疗信息和陌生人分享。而我现在在这间三百人的厅中也在做着同样的事,但当时,那件事让我感到不舒服,而她父母表示,让他们的女儿和我同住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我是同性恋,在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中长大,还住在南方,歧视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这个形式是以前没碰过的,且它非常让人失望,因为它是来自那么不可能歧视我的来源。他们不只受大学教育,他们不只也是LGBT社群的成员,他们还是我的朋友。所以,我照做了,我在学期末时搬出去了。但搬出去不是为了满足他们。而是出于对我自己的尊重。我不要让我自己臣服于那些不愿补救自身无知的人,我不要让现在已经成为我一部份的东西被用来当作对抗我的工具。
所以,我选择让我的状况透明化,永远被看见,不再躲藏。我把它称为「当个日常的倡导者」。这种透明化的重点,做日常倡导者的重点,是要消除无知,而无知是个非常可怕的词。我们都不想被视为无知的人,我们肯定不想被说是无知的人。但无知并不是愚笨的同义词。无知并非没有能力去学习。它是在你学习之前的一种状态。所以,当我看到来自无知之地的人时,我看到的是让他们学习的机会。我希望,如果我可以传播一些教育,或许可以帮助遇到类似像我室友状况的其他人,把情况缓和下来,帮其他人省去一些羞辱。
我得到的反应不全是正面的。在南方这里,我们背负许多污名,原因包括宗教的压力、我们缺乏全面的性教育,以及我们一般来说会用保守眼光来看任何和性有关的事。我们把艾滋病视为同性恋的病。全球来看,大部份新的艾滋病毒感染案例发生在异性伴侣间,在美国这里,女性,特别是有色人种女性,面临的风险在上升。这并不是同性恋的病,从来就不是。这是一种我们应该要关心的疾病。

所以,一开始,我觉得很受限。我想要扩展我的眼界,想要脱出围绕在我身边的一切。所以,很自然地,我转向了在线约会应用程序的黑暗世界,像Grindr这种应用程序,如果你不熟悉这领域,这些都是同性恋的约会应用程序。你可以上传你的个人信息和照片,它就会告诉你在一个半径内可联系的同性恋。你们可能都听过Tinder。Grindr的历史比它长很多,因为若想找个同性恋的未来老公相对难许多,不论在教堂、杂货店,或使用任何异性恋在发现能用手机约会前所使用的方式。
所以,在Grindr上,如果你喜欢你看到或读到的,你就可以发个讯息给对方,你们可以见面,可以做其他事。
所以,在我的个人信息中,我很明确写出我有艾滋病毒,我的病毒是检测不出来的,且我欢迎大家询问我的状况。我收到很多问题,和很多意见,正面和负面的都有。我想要从负面的开始,只是想表达我之前提到的无知。大部份的负面意见都是在提出评论或是假设。他们对我的性生活或是性习惯做出假设。他们会假设我让我自己及他人承受风险。但我经常遇到这种提出无知评论的人。在同性恋社群中,常常会听到「干净」这个字,指的是艾滋病毒检测结果阴性的人。当然,它反面就是不干净,或肮脏,也就是指有艾滋病毒的人。我并不敏感,我只有在田里一整天之后才会真的很肮脏,但这是种有破坏性的用词。这是一种由社群驱使的污名,让许多同性恋不敢揭露他们的状况,也让刚被诊断出艾滋病的人不能在他们自己的社群内寻求协助,而我觉得这点非常令人苦恼。但,谢天谢地,正面的响应更多,做出这些响应的是好奇的人。他们好奇想了解传染的风险,或是「无法检测出来」是什么意思,或是可以在哪里做检测,或是还有人会问我我的经历,我就能和他们分享我的故事。

但,最重要的是,会有刚被诊断出艾滋病的人来找我,他们很害怕,他们很孤单,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他们不想要告诉家人,他们不想要告诉朋友,他们觉得受损、肮脏。我会尽我所能立刻安抚他们,接着,我会让他们和AcadianaCares搭上线,那是我们社群当中一个很棒的资源,针对艾滋病患者的。我让他们联络我自身认识的人,让他们不只能找到一个再次感到自己是人的地方,同时也可以取得他们需要的资源,让他们能负担治疗。目前为止,这是我让自己透明化之后最谦逊的面向,我能够对和我一样受苦的人造成正面的影响,我可以协助在黑暗中的人,因为我也曾在黑暗中待过,那并不是个好栖身处。这些人来自各式各样的背景,当中许多人并不像我当时知道的那么多,他们是从恐惧的地方过来找我。这些人当中,有的我认识本人,或是他们听说过我,但更多是匿名的人。他们的个人信息是空白的,在发生了他们告诉我的那些事之后,他们害怕到不愿露脸。
至于透明化的这个主题,我想要留给各位几个想法,我发现,当我公开我的脸孔,不论我冒什么风险或赌上什么,任何负面评论都值得,我受到的任何抨击都值得,因为我觉得我能够造成这真实、有形的影响。它让我看到我们的努力得到回响,我们为善能够改变那些和我们相遇的生命,轮到他们用那动能向前更推进一步。如果你们或是你们认识的人正在对抗艾滋病毒,或是如果你想要知道你的社群内有什么资源,或只是想让自己学更多关于这疾病的知识,这里有一些很棒的全国网站,可以上去看看,也非常欢迎你们在这场演说之后来找我,问我任何你们想问的问题。
我们都听过「见树不见林」,我恳求在座所有人,真正去看到这疾病背后的「人」。只看数字和统计数据很容易,只感受到危险也非常容易。难的是看到这些数字背后的所有面孔。当你发现你自己开始思考这些事、这些话,当你看着戴维柯比时你可能会想什么,我请你改个方式,想想儿子,或想想兄弟,想想朋友,最重要的,想想人类。面对无知的人时,寻求教育,总是记得留心,总是保有同情心。
谢谢你们。

▲Arik Hartmann先生是一位自然主义者。他在路易斯安那大学(University of Louisiana)拉斐特分校获得资源生物学和生物多样性学士学位,目前计划攻读野生动物生态学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