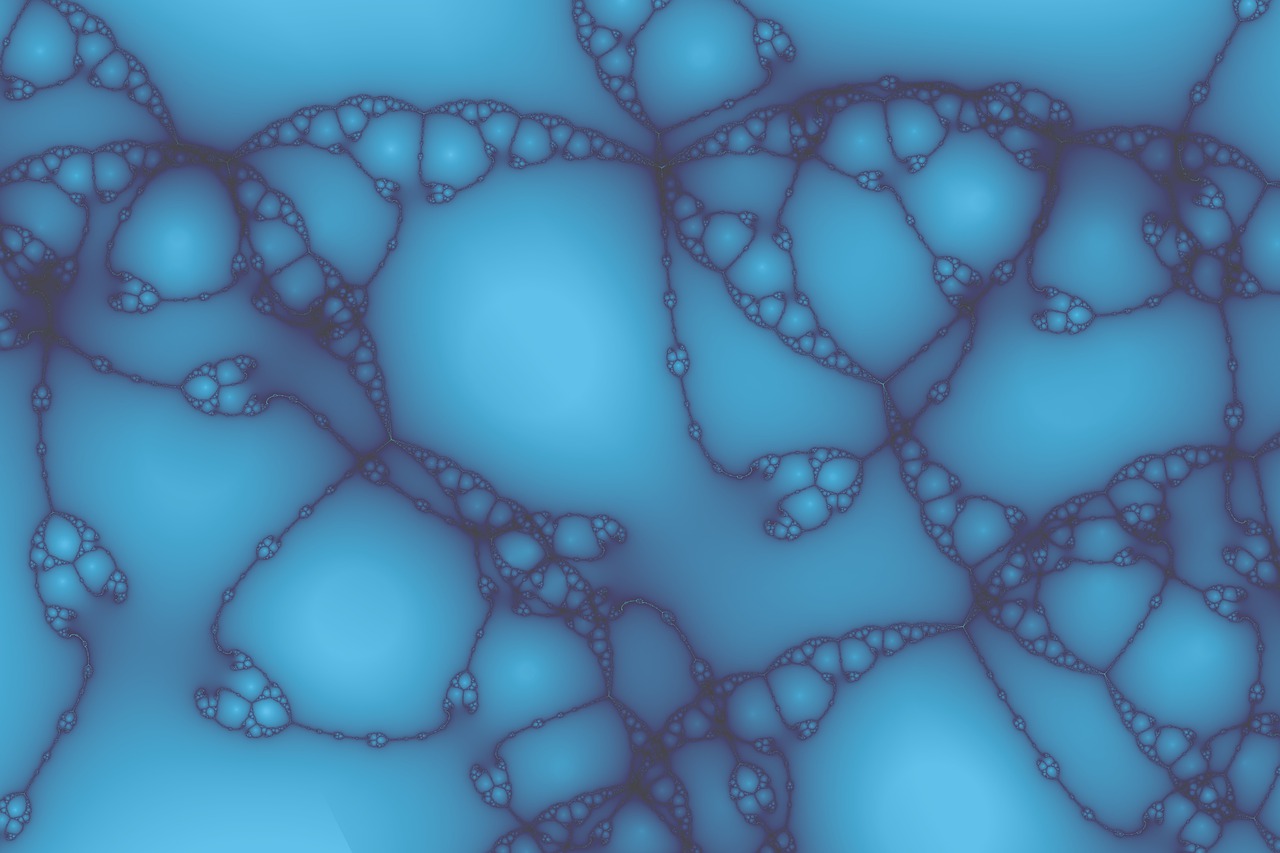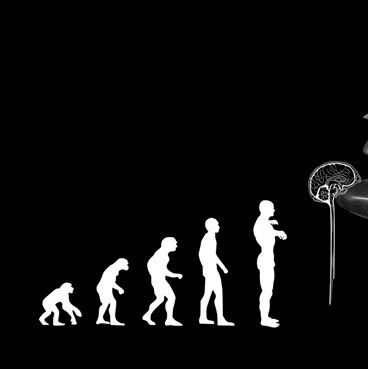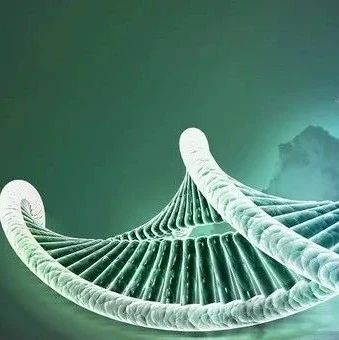每每提到动物议题,总有人会说:“我们现在连人都顾不过来还管猫狗”,“等有一天人都享有了该有的权利时再谈动物权利吧。”这种先后之分是不是真的理所当然?无数动物每天受到人类的残杀虐待,我们是否真能无动于衷?
我们都承认人类之间相互对待的方式是有是与非、对与错的,那么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又是否有是非对错之别?如果有,人类对动物应有怎样的道德义务?
以下是“Co-China论坛第二十三场:Co-China X I•CARE(一):动物伦理与道德进步”的文稿整理,由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编辑整理并授权东方历史评论转载。
讲者
钱永祥,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著名政治哲学学者,华人社会重要刊物《思想》总编辑,长期关注动物伦理与动物保护,并参与翻译《动物解放》、《动物权与动物福利小百科》。
梁文道,香港文化评论人、专栏作者,写作多次涉及动物的生存空间及人与动物的关系,如《全香港都是流浪狗的地盘》、《三花》、《距离》等。
主持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师。
演讲
钱永祥:首先,甚么是「动物伦理」?动物伦理或者动物伦理学所关心、想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有没有道德上的是非对错可言?我们知道,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的基本前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对待方式有是非对错可言,伦理思考帮我们判断个别行为的是非对错。把这个问题意识扩展到动物身上,我们想追问对待动物的方式有没有是非对错可言?动物伦理学给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理由是甚么?
大家对「动物」这个概念并不陌生。我们都是动物,叫作人类动物(human animals),那么非人类动物(non-human animals)在哪里呢?举目可及,先从各位身上的用品开始,皮鞋、皮包、皮带、皮夹是用动物的皮制作的;我们等一下吃晚饭,动物可能进入我们的胃里;我们吃的药、用的化妆品,几乎每一样东西都用到动物。动物在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可是他们存在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痛苦和死亡,动物只能以痛苦和死亡的方式进入人类的生活。
面对动物的痛苦和死亡,我们会怎样反应?怎样的反应才是合适的?让我们想象三个例子。我把一块石头踢到河里去、我把一根木头丢到火堆里去、我把一只狗打伤。对这三种情况,我们的反应不会一样。我踢石头、我烧木头,别人可能会觉得我很无聊,但是不能说我对石头或者木头造成了伤害;人们也不会特别对那块石头或者那根木头生出怜悯同情。与石头和树木不同的是,当我把狗打伤的时候,每一个人正常的反应都是认知到狗受到了伤害,并且对这只狗感到某种怜悯或者同情。
的确,动物是会受到伤害的,也会因此引起同情。根据一位哲学家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的分析,所谓对一个对象产生同情,代表你其实做出了三个判断。第一,这个对象在承受可观的痛苦;第二,这痛苦是他不应该承受的,是无辜的伤害;第三,你在乎这个对象受到了伤害。当我们说「我对你的遭遇感到同情」时,我们已经对这个人做出了这三个判断。但当我们对动物的遭遇感到同情、感到怜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三种判断呢?其实是有的。我们很明确地知道,第一,跟石头、木头不一样,动物会感知痛苦;第二,动物在人类手里所承受的痛苦根本是无辜的;第三,我们对于动物的痛苦,多少感到在乎。──但是,这个在乎是在乎到甚么程度呢?我们在乎的理由是甚么呢?我们通常会说:「不错,我同情猪的遭遇,我同情狗的遭遇,我同情实验室里小白鼠的遭遇──可是,它们毕竟是动物。」这意思是说,我们在人跟动物之间会划一条线,即使有同情有怜悯,同情和怜悯也要适可而止,至少不能妨碍人类的利益。
可是这条线要怎么划?能划得有道理吗?当代动物伦理学的奠基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认为,「划线」其实往往表现了歧视与成见。彼得•辛格将动物解放与另外两个重大历史运动相提并论:黑人及有色人种的解放、和妇女的解放。如果回到两百年前,当白人把黑人当奴隶用的时候,你问白人这个黑奴有没有在受苦,白人会说他当然在受苦,但是他还会说,虽然这个黑奴在受苦,但是他是黑人,他跟我们白人不一样。 回到一两百年前,女人被关在房子里,她们要受很多严格规范的约束,不能受教育、不能到外面工作、不能自己交朋友、没有社会生活、没有政治地位。你问男人你把女人关在屋子里好吗?他会回答是不太好,但她毕竟是女人,女人跟男人不一样。人们根据肤色划一条线,于是黑人的痛苦比较不重要;人们根据性别划一条线,于是女人的痛苦比较不重要。
今天时代变了,现在我们知道用肤色或性别在人之间划线没有道理。那么根据物种划线又有甚么道理?人这个物种与猪这个物种是有巨大的不同,但是这种差别,会造成他们的痛苦具有不同的份量吗?看到一只猪在受苦,我们会感到同情,可是我们会说:他毕竟是猪。可是猪的痛苦跟人的痛苦不都是痛苦吗?就像男人跟女人的痛苦都是痛苦,黑人跟白人的痛苦都是痛苦一样。我们不能说因为性别不同,两个痛苦就有不同的分量,不能说因为肤色不同,两个痛苦有不同的分量,那为甚么我们可以认为因为物种不同,两个痛苦就有不同的分量?人类到今天都不肯停止施加于动物各种痛苦和死亡,有一个很简单的借口:动物跟人不一样。但如果用物种划线可以成立,那用性别划线为甚么不能成立?用肤色划线为甚么不能成立?痛苦就是痛苦。穷人和富人的痛苦都是痛苦,男人和女人的痛苦都是痛苦,人类和动物的痛苦都是痛苦。不能说因为这个痛苦发生在与我不同的个体身上,所以我们就可以忽视。
如果动物的痛苦不能忽视,那么当我们开始谴责人类给动物制造痛苦和死亡的时候,我们就从同情和怜悯进入了道德的领域。在道德层面上,当我看到一个人受苦而感到怜悯同情的时候,我不只是在抒发一种情绪;进一步,对这个痛苦、对造成痛苦这件事,我还作了道德的判断,认为造成痛苦是有是非对错可言的,这是动物伦理学的全部关怀所在。
现在,我们来谈今天的第二个主题:道德进步。首先,我们需要追问,今天谈「进步」还有没有意义。今天各位想到生态浩劫、地球暖化、核战威胁、恐怖主义(以及反恐的恐怖主义),还相信人类有进步可言吗?
思想史学者常说,在1750到1900年之间,「进步」是在欧洲最有势力的观念。这主要是因为科学知识、生产力在当时开始突飞猛进,旧的社会政治秩序开始松动,思想观念也推陈出新,人们觉得世界正在改变,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并且有能力继续推动这种进步。但从1900年开始,进步这个理想逐渐破灭,到了今天,人们几乎已经放弃它了。有人说,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毒气与战壕让人们清醒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谈到进步会觉得尴尬,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进步」本质上是一个评价性的概念,进步一定代表「更好」,并且在道德意义上更好。可是几乎所有人类的广义「能力」,不管是文明、知识、科技、生产力等等,虽然都确实变得更丰富、更强大、更有效率、或者其他在量上的增加、质的改进,因此在这些意义上变得「更好」,但是由此要得出一个判断说,这些方面变得更好,就代表人类有了进步,表现了人类的道德进步,大家似乎都有点迟疑。毕竟,能力可以为善为恶,其增进可以造福也可以为祸。人类登上月球是进步,但这可以表示人类变得更好吗?人类有能力登月,但人类在地球上也更有能力相残作孽,并且变本加厉。所以在今天,各种能力的进步毫无疑义,可是人类对「进步」这个字眼本身,却感到毫无信心。
因此,要恢复「进步」这个理想,我们要从道德着眼,并且首先要确认道德意义上的「更好」要如何判定。但如果不谈一般的能力,专就道德本身来谈,有没有「道德进步」这回事呢?问题是:所谓的进步,当然就是从一个时间点到另一个时间点的历程,其终结点比出发点「更好」。可是今天流行道德相对论、价值相对论,正好不容许道德作为一套连续的、贯穿历史与社会阶段的标准。如果你相信相对论,你会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道德标准,每一个社会都有它的价值准则。你很难比较明朝人和汉朝人哪个朝代的人更有道德,很难比较美国人和中国人哪个民族的人更高尚,因为比较的标准都是内在于具体社会或历史阶段的。道德进步在今天的另一个挑战,来自价值多元论,即对于甚么叫做好的、值得追求的目标,每一个人不仅事实上会有不同的选择,并且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个人做不同选择的权利。我们无法用一个共通的标准比较甲跟乙哪一件事在道德上更高尚,所以也无从判断人们在道德上的表现先进还是落后。从道德相对论和价值多元论两个方面来说,好像都无从谈道德进步。
但事实的确如此吗?十九世纪一位爱尔兰的历史学家勒基(William Lecky),提出了「扩张中的圈子」(the expanding circle)的概念。他的意思是人类道德的发展,是一个「自己人」的圈子不断扩大的过程:我们列为「自己人」、受到道德考量的对象,最先限于自己的家族亲人,但随后会逐渐扩张到身边的朋友、自己的族群、阶级,然后扩张到同一个社会里的人、同一个民族的人,最后扩张到整个人类。勒基认为,圈子不断如此扩大,终于开始把动物和自然界也包括进来。「扩张中的圈子」这个概念,很明确地表达了一种「道德进步」:道德关怀的范围在扩大,受到道德考量的对象愈来愈多,就构成了一种道德上的进步。进步在哪里?在于以前受到漠视、歧视的人,以前被视作异己而提防、伤害的人,逐渐成为我们的同类,进入了道德考量的范围,从而其利益必须要受到我们的正视。我们列为同类的对象已经不受性别、宗教、民族和肤色的限制。今天的问题是: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再越过物种的限制,将道德考量的范围扩展到动物,让能够感受到痛苦的生命,也成为我们在道德上关怀的对象?
最后,我将动物伦理放到道德进步的问题脉络中来谈: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并不是孤立的一件事,而是人类对弱者、异类施加暴力满足一己需求的模式之一例。最近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出版了一本新书,题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为甚么暴力在减少?》,引起各方瞩目。平克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暴力逐渐减少的历史。他列举了六项趋势作为指标,其中第六项趋势谈的就是人类对于少数族群、弱者、他者异类的歧视与暴力,经由他所谓的「权利革命」,正在急遽降低。他举证历历,证明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对于少数族群的暴力、性强暴、家庭暴力、体罚、虐待儿童、校园的暴力、仇视同性恋以及针对同性恋的犯罪,都明显的在减少、甚至于被视为不可接受。这些权利革命中间最晚近的一项,就是动物权利。他的例证包括晚近以来关于打猎的电影越来越少,以狩猎为休闲活动的人越来越少,但是吃素的人却越来越多。这种趋势为什么可以视为道德进步的一环呢?那是因为无论是狩猎还是吃肉,背后的根本借口都是「动物不是人」,因此处于道德考量的范围之外;也因此,1. 动物的痛苦没有太多的道德意义,其利益无须列入考虑,以及2. 对动物使用暴力,无所谓道德上的是非对错。但随着「动物权利」意识开始散布,动物接续着女性、黑人、同性恋等等原本被排除在道德关怀圈子之外的弱者与异类,逐渐跨进了这个扩张中的圈子。在这个意义上,动物议题、动物伦理,正是人类道德进步的重要环节。当我们在考虑动物的利益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对待动物的方式有是非对错可言的时候,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便说得上道德的进步。
最后,让我举出一些事实,大家来想象一下,我们的日常饮食需要什么样的暴力与残酷为必经步骤。台湾每年要杀900万只猪,3亿5000万只鸡。中国大陆每个礼拜要杀1200万只猪,也就是一天要杀170万只猪,每一分钟杀1200只猪。不谈猪的痛苦,但我们想象一下:人类每分钟得施展多少暴力,才能把这1200只活生生的猪运送、宰杀、分解,最后贩售成为我们家人乐融融分享的盘中餐?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吃鸡蛋,可是鸡蛋哪里来的?鸡蛋是母鸡生出来的。母鸡哪里来的?母鸡是从鸡蛋孵出来的。鸡蛋孵出来的时候,公鸡跟母鸡的数量是一样的,那么另一半的公鸡到哪里去了?在小鸡孵育场里,刚出生的小鸡被一只一只地检查性别,母的准备送到养鸡场去生蛋,公的则丢到旁边的袋子里或碾碎机里,变成饲料或者肥料。再举一个例子。各位吃过小牛肉(veal calf)吧?小牛肉怎么来的?大家都喝牛奶,牛奶是母牛生产的。但是乳牛也有公的啊,生下来的乳牛如果是公的,就要变成小牛肉。怎样变成小牛肉呢?第一,生下来以后禁止运动,因为运动会使它的肉质变硬。第二,不准它接触任何有铁质的食物,因为吃了有铁质的食物,它的血红素会增加,它的肉就不是那种老饕欣赏的淡红色了。第三,对它使用大量的抗生素,因为它不能吃母亲的奶(母亲的奶含有铁质),抵抗力很弱。这样的公的乳牛生下来之后,饲养八到十四个星期然后杀掉,就是我们吃的小牛肉。
总结而言,我们的食物来自暴力,用血腥和痛苦为代价,我们吃的是「死亡」。清醒面对这个事实,才是道德智慧的开端。
梁文道:钱先生似乎颇为赞同平克的说法,认为人类是有道德进步可言的。但是钱先生最后讲到人类如何屠杀动物,又让我觉得我们好像这方面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电影《阿凡达》里那个星球的部落猎人在猎杀动物的时候,要一刀下去很快地割断猎物的喉咙,同时马上祈祷,让被猎杀者的灵魂进入宇宙能量循环。这个电影的灵感其实来自我们的祖先,甚至今天一些游猎部落仍然保有类似的习惯。他们绝不滥杀,像狮子一样。我们知道狮子吃饱了就吃饱了,面前有多少羚羊经过它都不理会。狮子绝不会想是不是该多抓一些羚羊回来,万一明天没得吃怎么办?能不能先把它们抓回来,然后想办法把它们做成罐头?狮子是不会考虑这些的,其实有些人类社会也如此。我读过一些人类学家的报告,他们发现一些古老的印第安部族有些奇怪的谚语,比如「当一头豹在吃小牛的时候,他的眼神是充满爱的」。这句谚语说明了那个部落对猎杀的看法:我猎杀我的猎物不是因为仇恨,而是生命的需要。但是我跟猎物都知道,我们迟早都要回到同一个循环里,有一天我的能量要回到这个循环里去滋养植物,植物又成为我的猎物的食物。纪伯伦的《先知》里有一段话很感人。他说我们在吃苹果时候,我们要对这个苹果说,今天我吃了你来滋养我的生命,但是有一天我终会回馈给你。这是人类曾经有过的想法。但是今天我们大规模地蓄养和屠宰动物,畜牧业早已成为一种工业,这是古代的人不能想象的。
我看过一部短篇科幻小说,这个小说很有趣,整个小说百分之八十你都不觉得是科幻。小说写的是一个家庭。小孩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妈问他: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他说今天谁谁谁因为做错了甚么事被老师处罚。再晚一点爸爸回来,妈妈在做饭,爸爸脱掉外套,一边喝啤酒,一边督促儿子做功课。然后晚上三个人吃晚饭,闲话家常。到了最后,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他们把他们吃剩的骨头扫进垃圾桶,那些骨头是人的骨头。但那些人骨很小,是迷你人吗?不是。这个小说讲的其实是一群从外星球来的巨人蓄养人类来吃。被吃的就是我们这种人,而他们是另一个星球来的殖民者。这部小说前面讲的是一个很温馨的家庭故事,但最残暴的部分恰恰就在这里,一个那么快乐、那么和睦,夫妻感情那么好,亲子关系那么愉快的家庭,他们的晚餐是我们人类。
我们在考虑为甚么动物应该有伦理、道德地位,我们为甚么要考虑动物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一个考量的范围。我刚才请教钱先生moral consider-ability应该怎么翻译,钱先生把它译成「道德的可考量性」。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决定要不要对一个对象产生道德关系,对其负有道德义务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这个对象具不具备被我们这样对待和被我们这么考量的资格,这叫道德的可考量性。曾经有一个神学家提出一个问题:人对神有没有道德义务?我们一般讲道德义务都是人对人的,那人对神有没有道德义务?又比如说人对树木,甚至对石头,我们有没有一个道德上的考量?
在这种讨论里大致包含三个层次的思考。第一,我们一般都认为我们应该,并且能够划出一个被纳入道德考量范围内的成员,一个「俱乐部」。凡是纳入这个范围内的,都具备了这种道德资格,不在这个范围内的就不具备这种资格。比如我们一般不会认为我们对石头要诚实,或者去想我不要伤害或者背叛它,我们不会有这个想法因为石头不在这个范围内。第二,我们也通常会认为有一个「我们」,是「我们」在划界:谁在这个范围内,谁在这个范围外,谁有这个资格,谁没有这个资格。第三,我们的社会有一整套成为制度的行为方式和规则来处理范围内所有的道德上值得被考量的成员彼此间的关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义务等等。
尽管哲学家一直在讨论,甚么样的对象有资格被我们道德地对待,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个范围其实不停在变化。比如钱先生刚才提到的黑人,曾经在白人看来黑人是不属于「我们」这个范围的。再比如在某些社会,老人也不在这个范围内,他们认为老人到了一定岁数就应该被遗弃,我们不舍得杀害他们的话他们就应该自杀,或者躲起来终结自己的生命。就像在电影《楢山节考》里老人被认为会拖慢整个部族的生活,最终会拖垮整个部族。似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人提出一些言之成理的说法来解释那个时代为甚么要那么做。他们会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不可以比较,不可以拿今天去看过去。所以我们不能够谴责古人残忍,他们把老人丢在山上让他们自生自灭;我们不能谴责白人在殖民美洲的时候,不止让黑人做奴隶,还使得美洲的原住民遭到灭绝。我们不要谴责他们,因为那个年代自有他们的一套伦理。我读大学的时候很相信这种文化相对论,我相信任何所谓真理的讨论都要放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的脉络中。但我年纪越大越相信这个世界是真的有一些真理,是真的有一些不可动摇的事情存在的。比如刚才钱先生讲到的受苦。受苦就是受苦,你看到被奴役的黑人受苦,那就是受苦。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争辩,我们可以说我们看到他在惨叫,我拿刀子划他的皮肤,他在流血,我划一刀他惨叫一下,但是,我不肯定这叫不叫做人类的受苦,因为在我的文化里面,我不一定能够把这解读为受苦。但真的是这样吗?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引入列维纳斯的哲学观点。
每当我们要定义人类的时候,我们都谈动物。比如我们常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言语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懂得欣赏美的动物」。我们每次定义人的时候都先有一个总的范畴——动物,然后把人从动物中切割出来,切割出来的标准或许是言语,或者是理性,或者是政治,或者是经济。有趣的是,自古以来哲学家在做这种划分的时候,他们都很快去谈理性是甚么、言语是甚么、智慧是甚么、政治是甚么、经济是甚么。他们都不谈动物是甚么。于是动物就成为我们悬而未决放在一边的X,我们都要用到它,但是我们都不想说它。这个令人尴尬的背景,在我很喜欢的一个哲学家身上也看到了,他就是法国20世纪的现象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列维纳斯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不同于其他的哲学家。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道德的可考量性,这样的问题总是要把资格赋予某个族群、某个类别。但是列维纳斯在谈论道德时,我们对甚么样的对象负有道德义务,跟他有道德关系的时候,他不去谈人类的本质,不去谈人要先具有的抽象的资格,他不会说我眼前这个具体的人由于是「人」的一部分,因此我对他负有道德责任或跟他有道德关系。列维纳斯不这样考虑问题,他考虑的从来都是最具体、最个别,几乎只是眼前发生相遇的场面,他叫做「in the face of other」,在他者面前,我们相遇。
他喜欢讲「脸」,在列维纳斯的哲学里,脸总是有表情的,它是在表达一些东西,有时候它表达出的是痛苦、是可被伤害。当列维纳斯在讲「脸」的时候,他关心的其实是遇到的那个具体的人,他能够表达他的感受,他可以被伤害。可被伤害性是列维纳斯一直很关心的问题,他觉得眼前这个人是可以被伤害,尤其是可以被「我」伤害。举个例子,如果我走过来揍你一拳,你会很痛苦,我会看到你痛苦的表情。这时候我跟你就发生了关系,你就有了要求我怎么对待你的权利。我要不要打你,我应该如何对待你,你是会对我提出要求的。列维纳斯永远关注的是在具体的情境下每一个个体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对他来讲所有的伦理(ethic)都是来自于原初的相遇。
列维纳斯有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他回忆了他以前的经历。他是犹太人,是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我们都知道海德格尔后来被很多人认为是纳粹的帮凶。而身为犹太人的列维纳斯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曾参与过抵抗运动,并因此被捕。列维纳斯跟一些犹太抵抗者一起被关在法国的一个战俘营,那个战俘营的编号是1492号。列维纳斯特别提到这点,因为1492年是天主教在西班牙掌权之后把犹太人驱逐出去的一年。他在文章中提到他们这些被关在集中营中的人觉得自己不像人,没有人的尊严,这不是因为吃不好睡不好,而是他们尝试跟看守互动,那些看守不理他们,他们这些人对看守而言不构成「相遇中的他者」,他们丧失了「他者」的资格。列维纳斯说他们是一群没有所指的能指,是一些空洞的符号,好像要指示甚么,但是甚么都没有。忽然有一天,在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人类资格的生活里,有一只狗出现了。这只狗是从战俘营外面的野地上跑过来的,它每天看着这些战俘白天去劳动,晚上回来。那只狗很奇怪,这些战俘根本没有甚么食物可以喂它,他们甚至不能去抚摸它,但是这只狗每天都看着他们,看到他们劳动回来之后就对他们摇尾巴,有时还会跳起来快乐地大叫,这是这个集中营里唯一会对这批犹太犯人表示善意的生物。他们给它起名叫Bobby。然后列维纳斯说了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Bobby是「the last Kantian in Nazi Germany」,纳粹德国最后的康德主义者。讲完Bobby的故事,列维纳斯笔峰一转,他又忽然说这只只狗没有聪明的大脑去帮它把自己的行为和倾向命令化,即把行为和倾向变成一个命令、一个道德义务。所以列维纳斯虽然笑称Bobby是纳粹德国最后一个康德主义者,但是他知道它其实不是。
可是我想补充和发展他的地方,就是凭甚么列维纳斯可以说Bobby对他们的欢迎不是道德上的交往呢?在那样一种极端状况下,这些战俘和他人相遇时人家不把他们当回事,但这只狗对他们表示出欢迎和友善,这叫不叫做「in the face of other」?这只狗跟他们的关系是不是道德关系?后来在一个访问中,有记者问列维纳斯他常讲的「他者」包不包括动物,动物有脸吗?他说动物有脸,但是动物的脸不如人类的脸那么重要,那么primordial,那么原初。
我觉得列维纳斯其实可以讲得更好。如果从他那种非常关注具体对象,从他者的表情读出痛苦这点来讲的话,他把动物放在次要的地位与他哲学的基本路线是矛盾的。他年轻的时候读达尔文,这对他影响很深,列维纳斯说所有的动物都在自利地追求生命的延续,而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动物都是处在all against all,彼此交战的状态,就像霍布斯(Thomas Hobbes)讲的那种自然状态一样。列维纳斯认为人当然也是动物,但人在面对他者的处境下会感到一种道德的无言要求,而动物不会。他认为只有人才能够跳出自己,「otherwise than being」,他讲的这个being我们不妨粗浅地理解为生物自我生存的奋斗和努力,natural being。但是为甚么是otherwise than being?列维纳斯讲我们人类超出生物求存的范围,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比如说可以为其他人牺牲,可以有种种利他的行为跟表现。如果我们只追求自我满足的话,我只要想办法好好生活,盖一个房子给自己,拥有房子里的所有东西,可以在里面过得很愉快。直到我遇到一个陌生人,遇到一个「他者」在冰天雪地里躺在路边,我忽然发现我的家不再只是我的家,它可以变成hostel,我发现我的所有品不再只是我的,还可以是一种gift。这种时候,人就不再只是一般的动物了。那么人为甚么可以这样呢?在列维纳斯那里这是一个miracle,一个神迹。
但是我们将他的说法应用在Bobby身上就会发现问题。Bobby是一只流浪狗,它有希望过从这些战俘那里获取食物吗?没有。他们从来没有食物给它,那Bobby为甚么还要对他们那么友善?Bobby为甚么还会看到他们就很高兴,想跟他们有一种互动?可见在这个故事里的Bobby恐怕不仅仅是列维纳斯所理解的动物的那种状态。我们太相信某种的人类中心主义,我们认为动物受到的伤害不是伤害,它们对我们的友善也不叫友善,或许这就如当初白人看到黑人受苦,觉得黑人的受苦不叫受苦一样。
我曾经养猫,每次我看着我的猫的时候,看着它看我,我常常在想甚么叫「它看我」?我说我和一个动物相遇,我说我碰到它的眼神的时候,这是甚么意思?这也是很多哲学家很困惑的问题。这能叫互相对视吗?我怎么知道那黑色的眼珠后面是甚么。我怎么知道对它来讲,看着另外一个物种的眼睛意味着甚么?两个人可以深情对望,那我能不能跟我的猫深情对望?我怎么知道它深不深情?我们总是试图去理解那个看不见的「动物的深渊」。你打一只动物的时候它叫,或者有另一些动物根本不会发声,比如说鱼。当厨师做刺身或寿司的时候,用刀一下子切到活鱼身上,你会看到鱼的嘴巴张开了一下,你听不到它的声音,那这叫不叫做「叫」?叫不叫做「痛苦地叫」?
列维纳斯的哲学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我们不要考虑这些问题。因为你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已经进入种类思考,就像我开始的时候讲的,这个个体具不具备某些资格,它有没有某些理性能力,有没有某些感知能力,它是属于哪一个族群,然后我才决定要不要道德地对待。列维纳斯认为这些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当下相遇的这一刻,这张脸呈现出的表情,如果它痛苦,如果它让我觉得可被伤害,它就跟我构成了一种道德的要求,我就已经负有责任。
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跟钱先生的观点一样,我也认为我们有道德进步,因为我们人类的确越来越具有看到痛苦脸孔的能力。我们曾经见过很多的痛苦,我们不把它理解为痛苦,但今天我们能认知到这种痛苦。
问答
提问1:我们谈动物,但动物到底包括甚么?您二位谈到的都是猫狗和哺乳动物,那草履虫算不算动物?吸血虫在吸我们血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对它有道德义务?
钱永祥:我们对草履虫有没有道德义务?我想,在考虑要怎么对待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们至少和这个对象要有些起码的互动可能,作为考虑的基础。有人说我们每走一步路就要踩死多少细菌、多少蚂蚁,这样的说法对人的道德意识要求太高了。当我们说不要杀生的时候,通常是指我们知道所杀的「生」大概是一个甚么状况。我们不能只提一个生物学上的生命定义,那是道德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举个例子,有人说癌组织也是生命,我们要不要消灭它?有人说蚊子叮你,你要不要打死它?当然要消灭,当然要打死。我们在考虑怎样对待一个生命的时候,那个生命本身总要有一套我们能够想象的意义。如果我们只能想象最贫乏的生命状态,坦白说,那不是人类的道德思考有能力照顾的对象。
提问2:我们为甚么一定要界定是动物,为甚么植物受到的伤害就不算伤害呢?为甚么折一支树枝就不叫伤害?难道伤害一定要是肉眼能够看到的吗?
钱永祥:我考虑它是不是能够感知痛苦,这也是彼得•辛格的定义。能否感知痛苦这点就把植物排除掉了。我们不要辩论说植物也会感知痛苦,以现在的知识,植物没办法感知到痛苦,植物会对各种外界刺激有反应,但那不叫痛苦。
梁文道:在印度文化中几乎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受到重视。自吠陀以来,很多宗教流派都有Ahimsa的概念,无伤、不杀生、无害,耆那教更是把Ahimsa的观念发挥到极致。他们认为植物的生命也应该被尊重,所以他们只吃死掉的植物。水果还在树上的时候是不能摘的,要等它掉下来了才能吃。
我们人类社会有各种各样的道德可考量性的标准,但是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要轻易地把问题转移到生命层级的问题,不要把它变成狗是不是比阿米巴虫重要,动物是不是比植物重要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要去比较这个,我们关注的就只有一点——痛苦。我刚才一直在讲列维纳斯,他就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关注的应该是那个对象会不会被伤害,它会不会表达出痛苦。仅此而已。
提问3:你们刚才讲到黑人平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动物解放运动的关系,我认为以种族和性别划分不同标准是不对的,但我觉得这些和动物保护还是有区别。妇女和黑人都是人,但动物不是。德国法学界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叫《为权力而斗争》,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就是权力是通过斗争而来的,而不是建立在同情和怜悯之上。人有斗争的能力,但动物显然不具备,所以这会不会决定了动物解放运动同黑人和妇女的平权运动没有可比性?人类的平权运动都是从「我」出发,「我」去斗争,「我」去表达,但是动物解放运动的主体是「它」。这种感觉有点像与虎谋皮,似乎得来的胜利果实随时会被颠覆。举个例子,我很爱动物,也提倡动物保护,但有时候我会说今天心情不好,我多吃点肉,今天累了,想补一点,又多吃点肉,这样一来,动物保护的成果不就很容易被颠覆,它的未来不就处于不稳定当中吗?
钱永祥:是不是因为动物不能抗争,所以争取动物权利的活动本身就不能与争取人的权利相提并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这个社会上的儿童、雏妓、智障人士、残障者、老年痴呆症患者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其他人帮他们争取权益,是不是仅具有怜悯与同情的含意?其实保护动物、为动物争取权利的时候,我们抗争的对象是谁?是我们自己。当黑人在争取他们权益的时候,女人在争取她们权益的时候,他们在为自己抗争,而我们在争取动物权益的时候,一个意义上是为动物抗争,另外一个意义则是减少人类自身的暴力和残酷。从这个层面上讲,动物保护运动也是把我们自己当成对象的一种运动。
你提到吃肉的问题,从动物伦理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应该吃肉。因为肉就是死掉的动物,动物怎么死的?被人类杀死的。为甚么杀它?因为你想满足口腹之欲。可是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想法,我称为「量化素食主义」(quantificational vegetarianism)。很多人吃肉的时候会觉得心里不太舒服,但是或许是因为习惯、天性,或许是因为文化、社会环境,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完全抗拒肉食。我碰到不少人说,他们愿意吃素但是又不敢,因为担心自己坚持不下去。我觉得,不要把吃素看成是一套绝对的伦理,它是有程度可言的。从伦理的角度看,一个礼拜吃一天素总比完全不吃好。您刚刚说心情不好或者累了想多吃点肉,那没关系,今天先吃一点,明天少吃或者不吃好不好?我们不要想把自己修炼成一个道德圣人。当然有人能做到完全素食最好,可我想大部分人都做不到。我跟母亲吃饭,她会做肉给我吃,我照样吃。我不会跟我母亲争辩说我不吃肉,你也不应该吃。我们对于动物造成的伤害,首要是一个量的概念。我刚刚讲到台湾和中国大陆屠杀动物的情况,我们几乎无法影响那个数字,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意识。我们都知道杀人是错的,杀一个人是错的,杀两个人也是错的,那我们会不会说既然都是错,我干脆多杀几个算了?当然不会,我们不是这样思考的。杀两个人的罪一定比杀一个人重,即使「不可杀人」是绝对的诫命,量的概念还是有关键的意义的。
梁文道:十六世纪欧洲有一些法庭,在那里动物的确是被列为可以接受传召的对象,动物可以上庭接受质询,甚至可能被定罪,而它们也有资格为自己辩护。当然我们知道从来没有动物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过,但是它们真的被叫上去过。这听上去像个笑话,但它背后包含的就是我们怎么思考动物在法律上地位的问题。它有没有法律权利?这个权利是怎么来的?依据是甚么?刚才您提到一定要有抗争才有权利,可是问题是我们把甚么理解为抗争呢?当你绑住一头牛要宰它的时候,它的挣扎是不是抗争?
提问4:如果我们想要保证动物让他们不受伤害的话,我们在政治上要不要给它们一些权利,比如投票权,让它们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
钱永祥:权利的概念和动物的概念,分别属于两个很不同的范畴,特别是当我们讲的不只是免于痛苦的权利,而是像投票权这样的权利,适用范畴当然很不一样。即使投票权利的适用,也预设了一些条件,比如某一些人类,因为某种残缺或者其他原因(「无行为能力」或者「褫夺公权」),就不能让他们拥有投票权。动物当然也不在这类权利的适用范围内。
梁文道:我们通常讲投票是因为我们假设我们在一个政治社群内,这个政治社群有一套决定事物的程序同方法。那现在的问题是,难道动物也是我们政治社群的成员吗?那为甚么不是每一个婴儿一出生就有权投票?可见要成为政治社群的成员需要一些资格,有一些要求,当然,这些资格跟要求和我们是否应该道德地对待他们不是一回事。
提问5:人的近亲黑猩猩就是杂食动物,肉是它们必不可少的食物。我当然觉得提倡素食挺好,但我认为吃肉是人的天性,就像狼会吃羊一样。你要提倡和人的天性对抗的道德法则,这必然遭到极大阻力。就好像我们说要平等待人,爱所有人,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像爱自己的亲人那样爱陌生人。
钱永祥:在某个意义上,道德一定要与天性对抗,虽然常常道德不敌天性,但顺着天性走就无所谓道德了。人本来就很脆弱,百万年继承下来的各种生物性需求,我们常常会受这些那些的因素影响,做了许多已知或未知的错事。天性是很真实的力量,所以我反对绝对伦理。但道德是甚么?道德是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去抵抗天性的控制。你提到狼吃羊,狼跟人最大的不同在于狼不太能够抵抗它的天性,而人类比狼更能够自我控制。所以,我们比较能够摆脱天性的直接控制。我们会说很坏的人像禽兽,其实禽兽的残忍程度比人类差多了。但因为禽兽抵抗天性的能力比较原始,我们才以为自己在道德上比禽兽高明。也因此,我们不会认为吃羊的狼犯了道德上的错误,我们不认为自然界里的动物是道德要求的对象,只有人才是。
梁文道:几乎所有我们熟知的道德条目都是在违反所谓的人类本性,那种自人出现以来就存在的不变的原始的永恒的天性是不存在的。如果你真的要说天性的话,那按照人类的天性,我今天看到一个女的很漂亮,我应该马上强奸她,让她给我生孩子。我为甚么还要去追求她?我们又有谁不是在违反天性?人类文明就是建立在对所谓天性的背反上,这才叫做人。另外,你刚才讲到猩猩,你读演化心理学就一定知道,天性是在演化中形成的。在演化过程中,我们不断修正自己,这个修正就包括对之前天性的违反。
提问6:钱老师说到不要给他者施加痛苦,要求人不要作为主动的施暴者。但是如果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施加暴行,作为旁观者我们也会有一种道德要求,要制止这种暴行。但是如果暴行是发生在动物之间的呢?比如说狼要吃羊的时候,虽然我们不能要求狼有不去吃羊的道德观,但我们应不应该去制止狼吃羊呢?
钱永祥:我必须强调,道德思考是考虑我们人怎么对待动物,至于动物之间如何互相对待,那不是道德能过问的问题。自然界当然不是一个道德世界,英国诗人丁尼森有谓:「Nature,red in tooth and claw」(大自然的牙齿与指爪血红)。动物世界充满了暴力,但我们不能把人的暴力和动物的暴力混为一谈。人类在做的事是故意的,是经过谋划的,是从暴力本身得到快感的。动物的暴力则出自于求生存的必要。在这个意义上,人犯错,动物充其量只是有过。
提问7:我们要善待动物没错,但生活从来不是这么简单。比如你面对一个非常饥饿的孩子和一只鸡的一个未及孵化的蛋,那你选择把这个鸡蛋给这个孩子吃呢,还是说你保存这个鸡蛋,然后让这个孩子饥饿?如果这个人保护了这个鸡蛋,然后让这个孩子饥饿的话,这个是道德上的进步还是退步呢?
梁文道:这一类问题似乎我们永远都会面对。这就相当于说你的丈夫和妈妈同时掉到水里,现在只能救一个人,你要救哪一个?做这种选择的时候我们会比较谁的价值更重要,或者谁对你更重要。这样的问题发生在动物身上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没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说你该先救动物,还是先救人,还是看他们跟你的关系。而这正是动物伦理学,或者广义的动物哲学重要的地方,因为这些问题会对我们造成困扰。我们人类面对动物的问题时会有很多知识论和形上学的困扰,这些困扰是真实的困扰,而这正正是我们要认真面对,仔细思考动物问题的原因。
提问8:刚才两位讲到素食和虐杀,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区分一下?比如同样是吃肉,但是食用通过很变态、很残忍的方式生产的小牛肉,和食用生长在自由的牧园上,然后一刀很痛快地杀掉的那种牛的牛肉是不是不一样的?
钱永祥:在动物的整个生命过程的不同阶段,我们如何对待它,的确是有意义的。彼得•辛格就说,传统农家的养鸡、养猪方式是可以接受的,平时它们的生活还算惬意,过年杀只鸡杀只猪,这没太大问题,我也赞同。我们对动物的痛苦是有量化概念的,一只鸡快乐地过了一生,最后痛苦一下,虽然我不是太喜欢这种事情,但我可以接受。
提问9:实验动物其实比一些用做食物的动物遭受更大的痛苦,但动物实验又是我们人类减少自身痛苦的必要方式。那现代医学的发展和动物伦理是不是有抵触呢?
钱永祥:在讨论动物保护的问题时,通常会把动物分成四大类:第一是同伴动物,就是家里养的猫狗;第二是经济动物,就是我们吃的、用的这些动物;第三是实验动物;第四是野生动物。你如果参加动物保护的团体,就会发现不同的动物保护团体在这四个领域的侧重都不太一样,因为大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在台湾和香港,并没有太多医学和生物研究机构,没有大规模的制药厂,我们基本都是从西方国家买药,所以实验动物的问题并没有像在西方那么严重。
回到您的问题,原则上,用动物做实验的研究机构和学术机构,都应该接受公众监督,因为他们不仅是在用社会资源进行研究,而且还是在用生命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是不是有充分的必要、是不是有充分的不可替代性,是要经过严格考量的。在欧美,一般会在从事活体动物实验、教学的机构,设立动物实验委员会,如果要进行动物实验,那就要把你的方案交给这个委员会来审核。最重要的是,这种实验动物委员会不能只由科学家组成,还要有兽医师和动物保护团体的人士参加。要尽可能避免科学家以科学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挥霍与折磨生命。
提问10:我们平常提倡动物保护的时候,很少有人说不要吃鸡、不要吃猪,大家说的是我们不要吃鱼翅、不要吃熊掌,因为这些不是产业化的东西,吃它们可能会造成物种灭绝。我们人类需要吃肉食,产业化会保护物种免遭灭绝,如果不去推行产业化,那可能会造成它们灭绝,但是产业化的生产方式也的确给动物造成很多痛苦。所以我想问的是痛苦和物种灭绝相比是不是一个更大的恶呢?
梁文道:我们饲养动物可以保护物种不被灭绝,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这就等于说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动物都应该被人养起来,这样它才不会灭绝,是这样吗? 的确有些物种是因为人类才保存下来的。比如伐木公司为了长期有木头可伐所以种植了某些树种,让这些树种可以一直存活下去。但伐木公司这么做绝对不是要保护这个物种,而是为了要让自己有一个长期可依靠的自然资源使用。这是完全不同的。
提问11:你们觉得养狗是不是不道德的事?
钱永祥:饲养宠物或者同伴动物,原则上说是把动物放在一个人造的环境里,逼迫它们脱离自然环境。在这个意义上,这的确是一件违反动物天性的事。可是有些动物的情况不一样,比如猫、狗进入人类的生活至少已有六千余年以上的历史,基本上猫狗脱离人类已经没法独立生活。我们不能把人家弄到我们的生活圈子里来,然后今天说人类饲养它们不道德。这是历史造成的后果,既然已经成为事实,我们就要承担。
梁文道:我建议我们把对某些物种的关系,比如说狗和猫,不要把它讲成是我们饲养它们,我们是主人它们是宠物那么简单。更多的时候这是一种共生的关系。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狗这个物种根本就是人养出来的,这等于说本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独立于人类之外的动物叫做狗。不只这样,人类养狗之后还促成了人类的演化。有一些生物学家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说话,之所以有时间坐下来聊天,发展出我们的言语功能,是因为我们安全了。我们为甚么安全?因为人类开始养狗,狗可以守护人类。所以人与狗在演化史上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共同演化关系。
提问12:不同的宗教对杀动物的过程都有一些要求,但是最终还是会杀害他们,那要是道德有高低之分的话,宗教是不是也有高低之别呢?
梁文道: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宗教高低的问题,但是大部分宗教都对自然界的秩序或生命的价值有一套看法,哪怕像伊斯兰教苏菲派的神秘主义者,或者是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他们都相信某种宇宙间的能量循环。他们会认为在这个循环中有一些事情是有利于循环的,另一些则不是,比方说滥杀动物,比方说在宰杀猎物的时候让它感受到多余的痛苦,显然都不是。但我们的问题是今天的社会没有一个稳固的、大家都可接受的对生命价值的共识,这也许就是今天人类进入一个最大规模杀害动物的时代的背景。
提问13:我们是不是把保护动物变成一个手段,让人类显得比较高尚,好让我们自己心安?
钱永祥:我们今天讲动物保护的话题,主要涉及动物的痛苦以及人类的暴力,我们关心动物不是为了减少人的暴力吗?我们减少人的暴力不是为了动物的福利吗?其实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们在乎动物,我们也在乎人。在乎人是希望人变得好一点,能够慢慢摆脱暴力的制约,同时我们也希望动物不要在人类的手里继续受苦。我不同意「手段」的说法,就像我们不能说禁止杀人只是为了让我们显得高尚的一个手段而已。
梁文道:康德说我们对道德负有义务。我们今天讲动物伦理,要对待动物友善一点,要减少暴力,这一方面的确是人应该追求的一种道德完善,我们要发现过去的盲点、我们的错误,然后纠正它。但是另一方面,这件事本身就是道德的。所以不是说我们要去做一些无关痛痒的事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们做这件事是因为对那个对象而言这本身就是道德的。我们不要觉得要不就是通过保护动物让我更好,要不就是为了动物自身的利益而保护它,不要把这两者对立起来。
提问14:刚才梁先生提出脸的问题,我想问蚂蚁有没有脸?如果我们看到蚂蚁也不忍心伤害它们,那这种感觉是更多来自我们自身的主观感受,还是来自那个对象?
梁文道:列维纳斯「脸」的概念固然是指我们可见的脸,但是同时指的也是一种遭遇。在一种遭遇下,一只蚂蚁也可以让我们感到它会被伤害,它会有诉求和表达。我小时候很残酷,拿水去淹蚂蚁,然后看到它们挣扎,那种挣扎就是痛苦的讯号,那我们就有不去伤害它们的道德责任。列维纳斯讲的是具体的处境,而不是物种。
提问15:梁先生刚才讲和动物对望的时候,就能感知对方的情感。我想问这会不会只是人情感的投射,还是你会知道那个动物在思考?
钱永祥:我家里原来养三只猫。1988年「妈妈猫」来了,1989年生下一只「女儿猫」跟一只「儿子猫」。「女儿猫」和「儿子猫」是在我的被子里生的,留下一摊血。2010年12月28日,最后那只儿子猫去世了。「妈妈猫」来的时候还没有断奶,「女儿猫」和「儿子猫」从来没有在外面跟别的猫接触过。这三只猫有两只是在我的床上出生的,有两只是在我的怀里去世的。这二十多年里我跟我太太从来没有一起出过国,因为家里一定要至少留一个人照顾猫,我们跟这些猫有非常多的互动。相处的二十多年,我非常了解这三只猫的个性。它们在跟人的互动中发展出非常不一样的反应方式和性格。你现在要跟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猫预知你回来在欢迎你?」我当然知道啊,这谁能跟我辩论呢?和这几只猫互动的经验让我知道它们的个性,也知道它们的感情,知道它们在乎的、恐惧的是甚么。
梁文道:去年有一个很有趣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是常拿动物做实验的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会议其实是谈大家的心理问题的,有很多心理学家和咨询顾问参加。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忽视的,就是在用动物做实验的实验室里受苦的不止是动物,还有人。其中有一个实验室的助理,他在会上一边说话一边哭,他说很对不起Dora。Dora是一只实验兔子,这个研究助理有一年多的时间每天照顾它,而Dora每次看到他进来也会在笼子里面跳,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然后他会喂它,抚摸它柔软的毛和长长的耳朵,他们的关系很好。但这个实验助理其实每天喂Dora吃的食物中都有一种慢性毒药,这个实验就是测试这种毒药的,那后来Dora当然死了。这个助理也因此病了。
我想说的是,假设眼前有这样一只兔子,我们抚摸它,我一进门它就会跳过来,那如果现在说其实它不是欢迎我,这只是我的想象,是我用人的角度投射在兔子身上。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就先将人和动物区分开了,然后想动物有没有情感,人和动物的互动模式是怎样的。这种思路是我们关于动物的讨论中常见的思路,我并不赞同。列维纳斯本来看到Bobby跟他摇尾巴的时候他感受到了友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处境。但是他后来偏偏又想到Bobby没有把行为上升到道德命令层次的能力。于是向他摇尾巴,跟他表示友善的Bobby忽然之间就不再是一个会对他构成道德要求的「他者」了。我不赞同这样的想法。我们不要先在脑子里去想它是一只兔子,兔子怎么可能会像人一样欢迎我们呢?这么想其实也就是在用人的自我中心的态度来思考问题了。
总结
钱永祥:人类在进行道德思考的时候有两大因素:一个是情境,一个是原则。道德思考其实就是在原则跟情境中间不断来回思考的过程。在具体情境中,我们尽量让原则给我们一些启发;思考原则的时候,我们让情境帮我们对原则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刚才一再强调不要给动物制造痛苦,你可以提出一千个情境来考验这个原则,也许有九百个情境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动物伦理学了。动物伦理学跟所有的伦理思考一样,是没有终极结论的。
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是我自己的经历。那是一九九几年,当时我们中研院经常来一些流浪狗,然后中研院会不定期地请台北市的捕狗大队把它们抓走。在这些流浪狗里有一只特别活泼可爱,跟人特别亲近,是一只大黄狗,我很喜欢它,就想不要让捕狗大队把它带走,想帮它安排一个去处。我认识一间动物医院的医生,我就问那个医生能不能帮忙安排,他说可以,可以送到一间他朋友的类似于动物养老院之类的地方。我回到院里跟那个狗说:我帮你安排了一个去处,我把车门打开,它就坐在车门口看着我。我说你进去吧,我帮你找了一个地方你可以安度晚年了,它自己就跳到车里去了。然后我就开车把它带到那间动物医院,那个医生说先放在这里,第二天就送它过去,然后就先把它关到一个笼子里。第二天我去看,它还关在那个非常小的笼子里,它畏缩在那里看着我,眼睛挂着很多眼屎。我就问那个医生是怎么回事,他说今天忙明天就送过去。那我第三天再去,狗去笼空,医生说那只狗死了。我问怎么死的,医生说它得了一种急性肠炎,他讲了一堆名词,我就完全呆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从动物医院出来,我开车回家,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在车里嚎啕大哭,我觉得我这辈子没有犯过这么大的罪。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原则性、概念性的东西。说到最后,也只有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稍微打开一点,就会发现很多动物会进来。草履虫大概不会进来,毛毛虫大概不会进来,因为我们也有我们的局限。我们不是圣芳济(St. Francis),我们没有他那种和各种动物都能沟通的禀赋。我看到一只蜘蛛,我分不清楚它哪边是头哪边是脚,你要我把生命打开跟它互动,我做不到。但我们可以跟很多动物互动。这不是说要大家一定要养狗养猫,或者一定要参加动物保护运动,一定要素食,不是的,只要我们把动物当回事,对它们多在乎一点,这就很好了。
梁文道:我小时候很残忍,常常去抓各种各样的昆虫,做标本或者虐待,甚至虐杀它们。有一次我抓到一只螳螂,然后又抓到一只很小的树蛙,我就把它们两个关在一起,看螳螂怎么对待树蛙。结果螳螂不管树蛙,这让我很愤怒。于是我就把树蛙抓起来送到螳螂面前,螳螂当然马上就用一个夹子夹住。那个小小的树蛙因为身体太柔弱,而皮又很韧,螳螂的刺刺不进它的身体,却把它的内脏挤压出来。那一刻我呆住了,然后我觉得很扫兴,不好玩,就丢掉了。从上中学开始,这个画面就不断在我脑海中出现,有一阵子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想起这个画面,它像梦魇一样困扰着我,我永远也不能忘记那个小小的树蛙死前和死后的模样,以及那个螳螂被我拿来游戏,让它杀害另一个动物的情景。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人可以有多残暴,而这种残暴有时候就是为了嬉戏。
我后来还干过很多坏事,但是这却成为对我特别具有道德意义的一个景象。我今天做时事评论、写文章,我对暴力、对残酷特别敏感,我好像能够感知到它们快要来了。那种敏感就是跟这个景象有关,是这个景象一直在提醒我。如果有人说那个树蛙只是吐出内脏而已,它的痛不是对人有意义的痛,这我完全没办法接受。那个场面对我的震撼太强烈了,我确切地知道那是痛苦,是伤害,是暴力,是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