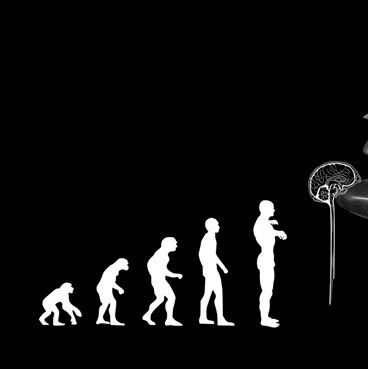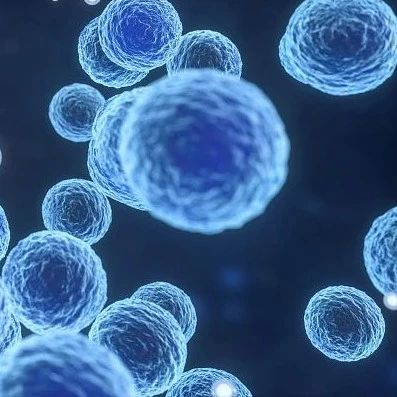健康君按:本文来自我们最受欢迎的作者之一鸭鸭(发送戒烟,读她的代表作《让我们戒烟吧》)。健康君读后,没出息地泪奔了。
面对疾病,辛苦的是甘愿埋首于实验台前的科研人员,是不分昼夜战斗在医疗一线的医生护士,更是那些饱受病魔折磨,却坚强勇敢,乐观宽容的病人和家属。
他们的精神激励着无数科研人克服困难,在未知的领域继续奋力探索。
谨以此文,向他们致敬。
谈到艾滋病,你会想到什么?
一种疾病,当涉及到性,同性恋,或者被社会歧视的边缘人群,人们难免刻意回避疾病的本源,把病因归咎在病人身上。
读小学的时候,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妈妈带给我一本漫画书,叫做《肉球谈艾滋病》。书中是一只叫“肉球”的胖胖的京巴儿讲艾滋病是什么,如何传播等等;讲得清楚易懂,老少皆宜。可惜这本书之后没有再版了。
但是我一直很喜欢这本书,也因此知道这个病是通过血液和性传播;清楚得记着何大一的鸡尾酒疗法,使得艾滋病从一个相当于“宣判死刑”的恶性病,变成了一个可以控制的慢性病。NBA魔术师约翰逊,也因此可以魔术般地继续健康活下去。他后来在唤起人们关注艾滋病,推广艾滋病的预防,反歧视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在美国从读博到做博后,从基础病毒研究到免医疗法,基因疗法,始终热爱着研究艾滋病的这个领域,无法离开。
从学术上来说,对艾滋病的研究发展极快,非常让人兴奋。但对我个人来说,这些年来因为工作碰到的这些病人和社会运动推进者(activist), 对我的人生态度产生了至深的影响。我今天想回忆的这些人,都不是纯粹的英雄主义。他们告诉我怎样摔倒,怎么拥抱一个不完美的生活。怎么哭完,再站起来。
Fred Hersch
2010年2月,我在旧金山参加一年一度的逆转录病毒学大会。
巨大的展厅里面坐着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我独自挑了一个比较靠后面的位置坐下。按照惯例,大会第一天会有一些表演,去年在蒙特利尔,因为赶上春节,搞了一个特别半吊子的舞狮子节目,所以我想万一没什么意思我可以轻易逃脱。
这次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爵士钢琴家,叫做Fred Hersch.

他消瘦得像一棵枯萎的树苗。站在讲台上摇摇晃晃,好像一阵风就可以吹倒了似的。他的嗓音沙哑,端着他的演讲稿,不看听众。我坐得那么靠后,都可以看到他的手在抖。
他早年患上艾滋病,但是等到了鸡尾酒疗法,活了下来。晚期服药的病人,通常即使药物非常管用,还是会有大量的潜伏病毒在身体中,身体状况也比较难于恢复到常态。
08年的时候,他的病情突然加重,进入了长期的昏迷,情况严重到医生和家属都开始怀疑他活下去的可能。
但是他终于醒过来了。他丧失了声音,丧失了活动的能力,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康复的希望,艰难地回到了生活自理并可以演奏演出的状态。
他在昏迷中梦到了许多东西。于是他把所见到的一切谱成曲,叫做Coma Dream, “昏迷的梦境”。这支曲子后来以一部爵士音乐剧的形式上演,轰动一时。
Fred Hersch在会上赞扬了不放弃他的爱人和医生,赞扬了成千上万的一线科研工作者,最后他说,我不会讲话,我还是为你们弹几首曲子吧。
他就坐在钢琴边,讲一个故事,弹一首歌,投入的时候会跟着音乐哼鸣起来。
我看过很多演出,但是这一场,是我迄今听到的,最美的音乐会。
他的梦,我都看见了。奇怪的形状。冰冻的湖。雾气。无声的呐喊。疼痛。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怨念。只有一种释然的美。其中有一首献给芭蕾舞演员的歌,他说喜欢看她们如此优雅地停在充满伤痛的脚尖上。
我坐在后面,默默地,流了满脸的泪。
对于爵士乐,我唯一的了解,是前男友借给的我一张CD,叫做“The night, with you”。我每次偏头疼病犯起来,觉得头骨要裂开,浑身发冷恶心无法行动,就吃一片止疼药,蒙着被子听那张CD,在琴声中等着疼痛淡去,知觉消失,慢慢睡去。
对我来说,那是安抚灵魂的声音。
后来才知道,那张CD是Fred Hersch录制的。
演出结束,掌声如雷。读博士的我便就这么浪漫地决定,博后也要继续留在艾滋病领域,希望哪怕能有一点微小的发现,一点微小的贡献。
Timothy Brown
对于一般人来说,他不叫Timothy, 他叫柏林病人。
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患艾滋病被治愈的人。
按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倒霉也是最幸运的人。他得了艾滋病,明明在服用药物后生活得很健康很好,但是倒霉地又得了一种很难治的白血病。唯一的办法就是骨髓移植。
他是最幸运的人,因为匹配的骨髓,恰好是CCR5delta32/delta32基因突变,简单地说,给他匹配的这个骨髓,因为产生了基因突变,缺乏艾滋病毒感染细胞需要的一个受体,因此是天然不会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
这样的概率比雷劈还要低,但是恰好让他赶上了。更幸运的是,他又恰好碰到了一个懂艾滋病的医生,能主动帮他找有CCR5受体缺陷的骨髓。
于是他就这样神奇地被治愈了。到现在,一直没有服药,还没有查出他体内有病毒跑出来。

作者在会上和柏林病人的合影
他的病例,在艾滋病领域是非常轰动的。这些年来,众多科研工作者,包括我自己,还有医生,都在探索如何通过基因疗法改造干细胞让其不被艾滋病感染,帮助免疫系统建立更强的抗艾滋病病毒的免疫力,用以代替神奇CCR5突变加骨髓匹配这样超级小概率的事件。
柏林病人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参观的时候说,如果让我选择得癌症但治愈艾滋病,或是不得癌症但不治愈艾滋病的话,我情愿不被治愈。
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媒体很少提,柏林病人其实有过两次骨髓移植,第一骨髓移植后,癌症又出现了,所以又做了第二次。每次都是很痛苦的过程。我们研究自体基因疗法也是为了减少骨髓移植的风险和痛苦。
Timothy在治愈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肯出来见媒体,最后他决定:“我不愿做那个唯一被治愈的人。”于是他站出来了,讲他的故事,为科学家筹集基金,呼吁社会关注艾滋病人,支持科学研究。他曾说,你们这些研究者,恨不得把我身体上所有部分都切一块下来测测。
这让我想起Stephen Crohn,一个先天不会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正因为他主动将自己交与医生和科研工作者,我们现在才知道了CCR5 delta32/delta32这种基因缺陷导致极少数人不会感染艾滋病,才了解到艾滋病的感染必需CCR5蛋白受体。
Stephen 晚年因为抑郁症而自杀。这些从屏风背后中走出,敢于告知大众自己疾病、决定贡献自己的人对我们每一个科研的进步,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但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痛苦?
这些年中有几次这样那样的以为是治愈的报道,但是最终还是以病毒胜利告终。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继续加油。
Charity Trek
这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

Charity Trek是一个公益组织。这几十个超级健壮的人,每年都会骑上百英里自行车来筹集善款,捐助UCLA和Emory两所大学的艾滋病研究工作。
去年夏天,我去做了志愿者。作为一个精力旺盛的疯丫头,遇到一群精力更加旺盛的半业余运动员,马上打成一片。
第一天要穿红色。为了筹集更多的钱,一位肌肉男找出蕾丝红裙,一天下来马上进入捐助榜前五名。
大家经常嬉笑打闹,但是那其实是多么艰难的路!上坡下坡,每天将近100英里。晚上睡帐篷,第二天一早又要出发,还要对付夏季里时不时的雷阵雨。

我学会了给自行车换轮胎,帮忙提供水和食物补给,以及各种啦啦队口号。
这些有着惊人体力的超人中,大部分是中年人,很多是艾滋病携带者或者家人朋友是艾滋病人。
他们的口号是,不到找到有效的疫苗,不到艾滋病治愈,我们不会停下来。
其中有些人是早期艾滋病爆发的幸存者,用到了好的抗病毒药得以活下去。不开玩笑严肃的时候,他们讲着讲着故事也会默默的流泪。第二天晚上在一位队员家的游泳池边,我们点了很多蜡烛,纪念那些离开的生命。我们抱在一起哭,擦干眼泪,天亮了继续上路。

一对超级恩爱的拉拉情侣,她们载着扩音器,放着超级放克的歌,一路都很拉风。
即使是现在的美国社会,在一些比较保守的人群中,对于同性恋和艾滋病人的歧视,还是很严重的。参加Charity trek的一位朋友Mishelle,拍了一部特别好的片子,叫做“And Counting”, 讲述一个参与骑行活动的艾滋病病人的故事。片子参加了很多独立电影节,我问她为什么不放在网络上让更多人看?她说:“孩子,从旁人的口中能说出多么恶毒的话,你恐怕还没有真正见识过”。
那些对他们有着那么深仇大恨的人们呀,你们有几个真正接触了解同性恋和携带艾滋病的人?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软弱,也有坚强的人。

缅因州的夏天
也是那个夏季的某一天,当我在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和缅因州美景间穿梭时,阳光灿烂,我喝着啤酒,听到了一个直到现在才能勉强面对的消息。
我的一位医生好朋友,离家出走,留下了遗书,很可能是自杀了。到现在仍然音信全无。
我一直特别喜欢这个朋友,他精力旺盛,跑马拉松,和我们一起露营爬山,喜欢同样古怪的动画节目。
可大家一直不知道他瞒着长期的脚伤和治不好的疼痛。我们只是知道他为此放弃了外科去做麻科,但不知道他因此患有很严重的抑郁。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还是去Charity trek两天前,给他讲我要去跑半程马拉松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不好的事情?”当时听了特别诧异,但是总也没想到他动了轻生的念头。
如果,如果他见到Charity trek的话……不能跑步,还可以骑车啊。还有那么多的路没有走过呢。说好一起去的。
如果我们能回到从前。
而听到这个消息后,要不是因为Charity trek的这些朋友陪我哭,拥抱我,我觉得自己当时大概要在缅因州的阳光下崩溃成碎片了。
这些四五十岁的人,年轻的时候因为同性恋离家出走,迷茫流离失所,有些因为艾滋病曾经一度完全丧失了生的希望,一度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但是他们现在成为了律师,教师,医生, CEO,慈善家,他们仍然因为这样那样的社会压力挣扎着,也和我们一样因为柴米油盐或者家庭感情的锁事发愁生气。
这些普通却又充满着英雄色彩的人,没有人觉得我的事情是小事,没有人说“谁没谁也能活”这样残忍的话。他们教我哭出来,再干一杯烈酒,教我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朋友,教我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活着。就是希望。就是我们要继续走下去的原因。
图片由作者及网络提供。
关于本文
封面和文内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作者鸭鸭,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分子免疫学博士,现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博士后,主要研究的方向是艾滋病和基因免疫治疗,同时拥有美国公共卫生认证书。
本文文字为作者原创,首发于公众号“清华医学中心”(thumc2012),授权发表于“健康不是闹着玩儿”微信公众号,任何其他媒体(包括线上线下平台和公众号等)申请转载,需联系“健康不是闹着玩儿”,联系邮箱:hi@jiankangkp.com
关于“健康不是闹着玩儿”
“健康不是闹着玩儿”:顶尖名校毕业的生物医学博士们,明明白白地把健康和疾病讲给您听。
关注我们,第一时间知道健康流言真假!
有问题,想加入我们,请联系:hi@jiankangkp.com
关注原创健康科普:长按二维码,或者请加 “jiankangkp”或者“健康不是闹着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