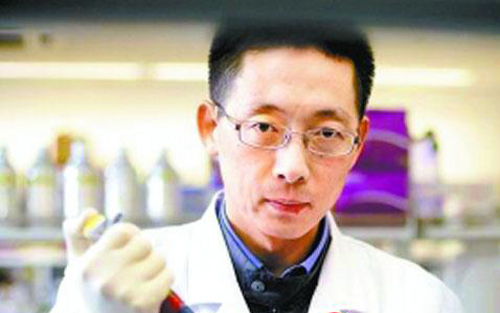
这是一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持续数十年最激烈的赛跑,中国科学家以一次完美的撞线赢得了胜利。
2014年6月29日,英国《自然》杂志以长文形式在线发表了这个让全世界顶尖生物学家都为之一震的惊人发现。它也是罕见的,让世界顶级期刊《细胞》《科学》“疯抢”的重大成果。
“我很紧张。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4天之后,7月3日,清华园夏意正浓,大名鼎鼎的施一公在媒体的注视下略显羞赧,疲惫的嗓音却透出轻松,“这次不是杂志选择我们,是我们选择了《自然》。”
“阿尔茨海默症多发于65岁以上的老人,随着现代人寿命的增长,患病人数将越来越多。20世纪90年代末,科学家就知道了人源γ分泌酶复合物是其致病蛋白,但几十年来,却从未有人看清它到底‘长成什么样’。”他在试图用最浅显的语言向普通人揭示这个令人激动的发现,“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人类首次看到了这个蛋白质的真实形状、组成和几乎所有的二级结构。”
“这是我科学生涯里最耀眼的成果。甚至超过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所有成果的总和。”归国六年,生活在“聚光灯”下的施一公一向用词严谨,今天却破天荒地用这样的评价为这个成果注脚。
拼搏,夜以继日,“白手起家”却领跑全球
这是一个藏在施一公心里3个多月的秘密。
2014年3月,刚刚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晶体学领域国际最高奖项——爱明诺夫奖的他,一下台就被同行小声追问,“一公,你们是不是在做人源γ分泌酶复合物的结构研究?”三个多月后,世界生命科学领域名气响亮的冷泉港结构生物学研讨会上,面对4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以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公布了这个让无数科学家都为之“玩儿命”的重大发现。
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据统计,该症已是发达国家花费最高的疾病之一,我国目前约有500万该症患者,占世界发病总数的1/4。而到2050年,估计全球每85人就有1人罹患该病。
“人类曾经花了很大气力鉴定老年痴呆症的起因,终于找到γ-分泌酶是最重要的‘罪魁祸首’。可一直以来的结构研究却屡屡碰壁,在结构决定功能的科学世界里,如果连这个蛋白长什么样都看不见,就很难解释它的发病机理,更别提药物研究了。”如今,获得γ-分泌酶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已成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很多做结构的人都想去碰一碰。就像买彩票,明明知道有个大奖放在那儿,口袋里有点钱的人都想试试。”
早在2004年,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施一公就把目光锁定了这个全球科学家都“心照不宣”的结构生物学制高点,但研究却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人源γ-分泌酶很难获得,只能在果蝇、线虫等类似物结构中做,一点儿进展都没有,非常痛苦。”
2008年回国后,施一公迅速组建实验团队,也把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的梦想带回了清华。
这是一个除导师施一公外,完全由年轻博士生组成的团队。27岁的年轻博士生马丹和26岁的卢培龙是夫妻,他们俩和远在伦敦求学的好友清华毕业生白晓晨一起,共同组成最核心的力量,此外,还有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谢田、闫创业、孙林峰、杨光辉、赵燕雨和周瑞。
“要进行结构鉴定,最关键的一步是获得纯度高、化学性质均一稳定、有活性的人源γ-分泌酶。但它是存在人脑中的,我们根本不可能从人体中取样。如何把这个蛋白表达出来,是最难的突破点。”施一公把组里的8个学生分为3个小组,他们泡在实验室里,从细菌、酵母、昆虫细胞等多个表达系统中寻求突破,并最终选择了哺乳动物表达系统。
回忆起那段岁月,马丹说有种“快乐的充实”,“在这之前,整个学院关于哺乳动物细胞悬浮培养的经验非常少。我们就自己上网找文献,还跑去一些卖耗材、制药的、做细胞表达的公司去看仪器,学习养细胞的经验和方法。施老师也请国外的专家给我们做讲座,就这样一步步摸索总结过来。”
经过大量系统的尝试,以及对表达和纯化方法的不断改造和优化,历经数年,他们最终利用瞬时转染技术在哺乳动物细胞中成功过量表达并纯化出纯度好、性质均一、有活性的γ-分泌酶。通过与英国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合作,对获得的复合物样品进行了冷冻电镜分析和数据收集,最终获得了分辨率达到4.5埃的γ-分泌酶复合物三维结构。
“好比国外科学家在100米外看一个馒头,而我们在5米外看一个馒头。相比此前的外国科学家只能将该蛋白酶解析到12埃的分辨率,这让世界科学界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向前跨出关键性的一步。”
夜以继日的拼搏,终于让“白手起家”的中国科学家领跑全球。
科研的态度就是:坚持、协作和担当
“生平第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言简意赅地介绍完重大成果,施一公骄傲地把在场的所有团队成员一一介绍给媒体。这是比这个世界级的研究成果更让他珍视的“作品”,“我毫不怀疑这些年轻的学生大多数会脱颖而出,成为优秀的青年科学家。”
而在学生们的眼中,有一个永远给他们“打鸡血”的施一公:一大早走进实验室,他就等在那里,兴致勃勃地准备与学生讨论课题。一个看起来简单的生化结果,会突然激发他无限的灵感。
学生们都说:“施老师不仅教给我们科研的方法,更让我们学会了科研的态度,那就是坚持、协作和担当。”
“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去找他,都会从他那里获得无限的激情,什么灰心丧气都没有了。”2013年10月的一天,马丹和卢培龙遭遇了实验中最惨痛的挫败,辛苦养了一个多月的细胞在进行最后转化时,摇床却突然坏了,“一摇床的细胞摇瓶,碎得到处都是,满床都是玻璃”。是施一公的宽慰让欲哭无泪的她重燃斗志,“科学研究从无坦途,那么多科学家苦苦较劲的世界级难题,哪能随便成功?”
这个课题就像打仗一样,需要与时间赛跑,这让一向和蔼的施一公有时也变得严厉。2014年春节,新婚的马丹和卢培龙硬着头皮请了三天假回家见父母。可返校后,还是被他说了几句,“实验室还有7位同学都在这儿过的年,到这个份上了,必须玩命。”
每天都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的他,总是向学生强调从事基础研究应有的担当,“全世界都在为科学研究争分夺秒。当你读到经典文献,听到同行又取得了重大成果的突破,甚至每听到一个精彩的学术报告,有鼓舞,但更深的是来自心底的压力和不安全感。基础研究是一个国家腾飞的引擎,科学发展这么快,你在科学上的作为在哪里?你对国家的贡献又在哪里?”
如今,面对众多赞誉之声,每一位成员都在强调团队的意义,“科学研究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协同创新才能有大的突破。”
奇迹诞生的根源:瞄准最前沿的世界课题
早在2008年,《纽约时报》就这样报道施一公的回归:“施一公和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回归是一种信号,中国在拉近和发达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上,比许多专家预期得要快。”如今,施一公和他的同事们,以一个又一个的重大科研成果,让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
仅仅是一个月之前,清华生命科学学院的年轻教授颜宁刚刚在同一地点发布了另一个世界级的科研发现:首次破译人体能量转运通道,成功解析了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的晶体结构。
奇迹,为什么能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
施一公说,今天所有的成就,是他自己在回国前都“始料未及”的。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待遇和科研条件毅然回国的他,被很多人认为“疯了”,“连我在美国的亲戚都觉得我脑子有问题。”可他说,自己现在的心情却“前所未有的舒畅”,“当时也有过很多担心,担心学生质量,担心科研设备。但现在,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实验室的总体水平、做科研的深度、系统性等,已经全面超过我在普林斯顿最鼎盛时期的水平。”
事实上,6年来,施一公在科研上的贡献显而易见: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学科从只有40多个独立实验室增加到了120多个;被他引进到清华全职工作的世界范围的优秀人才多达70余名。他自己也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级的期刊上发表了15篇学术论文。
总结自己、团队和同事的成功,施一公认为有三条:一是有一批优秀、努力的学生;二是不再囿于论文、课题的压力,瞄准的全部都是最前沿的世界级课题;三是得益于良好科研环境的支持。
如今的他,尽管已经站在了全世界结构生物学研究的制高点上,却仍然时刻保持着拼搏的警醒和担当。
“我们的目标是得到更高分辨率γ分泌酶复合物的结构,这样就可以精细地解释,任何一个引起老年痴呆症突变的氨基酸突变是如何导致γ分泌酶复合物切割A42的肽段,这样就可以根据结构来设计药物分子,这是一种愿景吧。”
“不能只把眼光盯在现在的成功上。别忘了,中国的整体创新力还只排在世界20多名。要是在所有的科研领域都能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那我们的国家就真得不得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