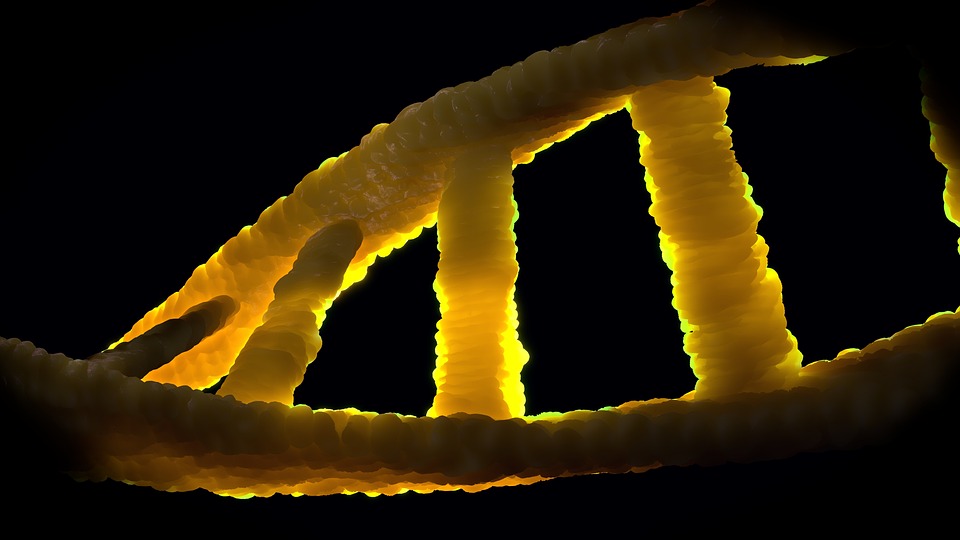本文转自医药魔方数据微信,发布已获医药魔方授权,如需转载,请与医药魔方联系。
2008年9月,Corey在接受基因治疗4天之后,抬头望向费城动物园的上空,第一次看清了那些五彩斑斓的热气球。八年之后的2017年10月12日,Spark Therapeutics的RPE65基因疗法产品Voretigene neparvovec以罕见的16:0投票比获得了全部FDA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支持,赞成其上市用于治疗RPE65突变引起的莱伯氏先天性黑蒙症 (LCA)。虽然基因疗法已经开始显现它的巨大威力,然而医学领域的突破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基因疗法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经历了极为曲折的发展历程,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I
人类的疾病可以粗略地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由遗传因素主导的疾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遗传病。大多数遗传病的发病率非常低,通常在千分之一到百万分一之间。第二类疾病是由于环境因素主导的疾病 (受遗传因素影响的程度非常小),比如细菌感染,病毒引起的普通感冒,以及骨折。而第三类疾病则是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主导的疾病,比如癌症、高血压。
很多类似普通感冒等由细菌或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由于抗病毒药物、抗生素的存在以及人体强大的免疫系统的作用可以被完全治愈。而类似高血压,阿尔茨海默病等由多基因以及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疾病,以现在的医学水平想要实现治愈是极其困难的。那么单纯由遗传因素主导的遗传病其治愈会不会很困难呢?
遗传病通常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单基因遗传病,多基因遗传病和染色体病。相比多基因遗传病的多个基因共同参与,单基因遗传病只是由单个基因突变引起的疾病。由于病因相对清楚,单基因遗传病看起来并不像癌症高血压那样复杂,所以很早以前科学家们就有疑问:既然遗传病是由基因异常引起的,那么通过对基因缺陷进行修复就很有可能治愈该类疾病。
其实早在沃森和克里克提出DNA的双螺旋结构之后不久,就有人设想运用基因改造来治疗遗传病。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确定基因疗法这一概念的具体提出时间,但一般被认为基因疗法是从1967年开始被讨论并引起关注的。Marshall Nirenberg在当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到利用合成信息来编码细胞的概念,并对基因疗法潜在的有效性进行了讨论。
1970年初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医生Stanfield Rogers开始了第一次尝试。Rogers此前一直专注于兔乳突病毒 (Shope papilloma virus, SPV)的研究,SPV是一种能够使兔皮肤长出肉疣的病毒。Rogers很早之前就发现SPV感染的兔体内会生成异常的精胺酸酶,而且他们怀疑该病毒能够将编码精氨酸酶的基因整合到宿主细胞上从而表达该酶。此后他们又发现SPV感染的兔血清精氨酸水平下降,于是Rogers决定开始尝试研究SPV病毒的疾病治疗潜力。
巧合的是1969年和1970年《柳叶刀》等杂志报道了一种最适合验证SPV病毒疗效的疾病。文章中报道的三位儿童出生在一个德国家庭,他们长期以来饱受神经系统病症的困扰,并且发育迟缓。医生发现这三位儿童血清精氨酸水平非常高,而且细胞内精氨酸酶活性下降。这种疾病称为高精氨酸血症。
Rogers与德国的一位医生合作,尝试利用系统注射SPV来治疗高精胺酸血症。但在1975年,Rogers发表文章称该基因疗法的临床试验失败。后来证实SPV并不携带SPV基因,而且尽管Rogers把SPV称为疣病毒,但该病毒却能诱发人正常细胞癌变。该试验算是一个乌龙事件。由于当时人们对于SPV导致血清精氨酸水平下降的机制以及高精氨酸血症疾病本身的了解太少,临床试验失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上世纪70年代重组DNA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基因疗法技术的进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基因疗法的第一次真正尝试是1980年在UCLA的Martin Cline主导下进行的。 Cline在没有得到机构审查委员会 (IRB) 以及其他机构审批的情况下,擅自使用DNA重组技术将β-地中海贫血基因转入两名意大利和以色列患者的骨髓细胞中。尽管Cline对外称在6个月后患者体内依然存在具有活性基因的细胞,但该说法并没有得到验证。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该临床试验同时也给Cline本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使他被迫卸任了系主任的职务,也失去了很多项目经费支持。
早期的基因疗法之所以首选β-地中海贫血,是因为当时对于血红蛋白和贫血的研究比较清楚。但后来却发现β-地中海贫血的治疗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血红蛋白由两条alfa链和两条beta链组成,而两条链分别由两个基因编码。β-地中海贫血是由HBB基因突变导致的,想要达到理想的治疗目的必须使血红蛋白同时具有两条正常的beta链和两条正常的alfa链,而且修复的细胞需要达到一定占比才能够显示贫血治疗的效果,所以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为了更容易验证基因疗法的有效性,必须寻找治疗相对容易的遗传病。而腺苷脱氨酶缺乏引起的重症联合免疫缺陷 (ADA-SCID)正符合这一条件。ADA-SCID是由于腺苷脱氨酶缺乏导致的,由于该酶的缺乏使核酸代谢产物异常累积,使T、B细胞功能障碍引发严重的免疫缺陷。
1990年,在经过繁琐的FDA审查和批准之后NIH的William Anderson终于可以开始针对重症联合免疫缺陷基因治疗临床试验了。而这一次,基因疗法终于迎来了第一次胜利。
II
1989年的时候,4岁的Ashanti DeSilva已经奄奄一息。她被诊断患有ADA-SCID。和所有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症的患者一样,Ashanti的免疫功能几乎全部丧失。对于Ashanti来说,这个世界似乎总是充满恶意,与别人的每一次接触,触摸每一件东西都有可能引发致命的感染。从出生起,她一直经受感染的折磨,到四岁的时候她身高体重只有两岁儿童的水平。
ADA-SCID的标准疗法是注射一种人工合成的腺苷脱氨酶PEG-ADA。虽然刚开始注射的时候药物的疗效会非常好,但腺苷脱氨酶注射疗法通常会渐渐失效。Ashanti两岁的时候开始使用该药物,到了四岁的时候药物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被告知无法进行骨髓移植之后,她的父母陷入了绝望。在这之后,Ashanti的父母遇见了计划进行基因疗法临床试验的Anderson。
基因疗法确实存在风险,但Ashanti已经别无选择。1990年9月,Anderson和同事开始对Ashanti进行基因治疗。在长达12天的治疗周期中,他们首先从DeSilva体内抽取血液,提取其中的淋巴细胞,然后利用改造后的MoMLV将功能正常的ADA基因插入这些细胞的基因组中。9月14日,医生们把这些细胞回输到Ashanti体内。
基因疗法的目的与骨髓移植大致相同,但基因疗法的优势是不会产生免疫排斥反应。Ashanti这次治疗的效果非常显著,六个月后,她的T细胞水平就恢复了正常值,之后她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好。几年之后,她终于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上学了。终于,她可以和其他小朋友玩耍,可以有一个相对正常的童年了。
但Ashanti并没有被治愈,她仍然需要使用低剂量的PEG-ADA。尽管如此,这一次的基因治疗验证了基因疗法的潜力:我们可以通过对基因组缺陷进行改造来治疗遗传病。随着Ashanti治疗的成功,基因疗法也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春天。

22岁的Ashanti DeSilva
1991年另一位患有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症的11岁女孩Cindy Kisik在同一家医院接受了Anderson医生团队的基因治疗。1992年底,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中心的James Wilson医生宣布,他的团队成功治疗了一名患有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 的29岁女性。
自1990年开始,全世界有数百个实验室加入到了基因疗法的队伍之中。有超过4000位病人参与了大约500个临床试验。而该领域的基础研究也显示基因疗法有可能被用来治愈糖尿病,镰刀细胞贫血,以及多种类型的癌症,甚至可能用来扩张堵塞的动脉。而动物实验也表明基因疗法有可能提高实验动物的活动能力,因此有人也提议用基因疗法来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
这是一场医学的狂欢,也可以说是一场闹剧。然而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却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在经历了将近十年的兴盛之后,一盆冷水浇灭了基因疗法炽热的火焰。
III
站在莱特森山的最高处,可以看见远处荒凉的峡谷中星星点点的仙人掌。穿越峡谷,便是一片茂密的松林。人们常说那里是亚利桑那州离天堂最近的地方。Jesse Gelsinger很喜欢那里。也正是在那里,十一月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在基因疗法夺走了18岁的Jesse的生命之后,他的父亲Paul Gelsinger将他埋葬。
Jesse出生于1981年,像其他小朋友们一样,小的时候他也非常活泼可爱。但他的父亲Paul却发现Jesse有一样毛病,他非常挑食,只吃土豆和麦片,从来不吃肉类和奶制品。Jesse在两岁八个月的时候得了一场感冒,在这之后他的性情急剧变化,就像一个呆萌的小朋友突然进入了叛逆的青春期,与别人交流的时候充满了攻击性。之后Jesse的父母带他去看儿科医生,而医生说他只是贫血,多喝点牛奶就好了。然而Jesse的身体反应却告诉他的父母Jesse应该避免接触该类食品。
在一个周六的早上,Jesse突然陷入了昏迷,Paul急忙把他送到了费城儿童医院。血检之后发现Jesse血氨水平过高,医生说他患有雷氏综合征。但雷氏综合征通常与服用阿司匹林相关,他的父母并不相信医生给出的这个诊断。一周之后Jesse最终确诊,Jesse患有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陷症 (OTC syndrome)。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发病率大约为四万分之一。由于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使尿素循环通路出现异常,导致Jesse的细胞内氨基酸分解代谢出现异常,血氨水平升高,从而导致神经系统毒性反应,这也是Jesse出现昏迷的原因。
所幸Jesse是胚胎发育时由于自身基因突变导致的该疾病,只有部分体细胞存在该基因缺陷,所以他的病情较轻,通过严格的控制饮食以及药物治疗,Jesse磕磕绊绊地长大了。到了17岁的时候他的主治医生向他提起基因疗法的临床试验可以治疗他的疾病,但他却不太感兴趣。虽然需要严格控制饮食,有时候甚至每天需要服用50个药片,但他的疾病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发作了。

Jesse Gelsinger
但Paul却发现他有时候会漏服药物。圣诞节前夕,Paul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Paul那晚回到家,发现Jesse痛苦的蜷缩在地上,呕吐不止。Paul立即将他送往医院,血检发现他的血氨水平超过正常值6倍,随后的几天Jesse的情况并没有好转,一度呼吸停止。所幸之后他度过了鬼门关。1999年的新年过后Jesse出院了,此时他也满18岁了。
Jesse的主治医生再次跟他提起了基因疗法的临床试验。但这次试验只是为了验证病毒载体的安全性,该病毒载体并不携带OTC基因。尽管如此,如果该疗法临床试验成功的话,将有可能帮助Jesse和其他儿童摆脱疾病的困扰。最终Jesse同意参加临床试验。
1999年9月13日Jesse接受了病毒注射,之后他便开始并陷入深度昏迷。随后几天之内他的多个脏器出现衰竭。9月17日Jesse被诊断为脑死亡。Jesse的死亡与临床试验的违规和过失不无关系,他的死亡也对整个基因疗法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使这股热潮迅速冷却。
然而祸不单行,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再一次使基因疗法坠入了深渊。
IV
X染色体连锁重度联合免疫缺陷病 (SCID-X1)与ADA-SCID类似,也是一种重度联合免疫缺陷病。但SCID-X1的病理机制与ADA-SCID不同,由于编码T细胞表面白介素受体gamma链的基因异常,使白介素受体功能缺陷导致免疫机能严重受损。ADA-SCID与SCID-X1都能够通过骨髓移植进行治疗,恢复免疫细胞的正常功能,所以理论上SCID-X1也能够通过基因疗法进行治疗。
1999年法国内克尔儿童医院的Alain Fischer准备使用基因疗法治疗患有SCID-X1的儿童。Fischer采用与Ashanti所使用的类似方法,首先对一位11个月大的婴儿进行了治疗,紧接着治疗了另一位八个月大的婴儿。两名婴儿在住院的三个月期间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而且病情并且明显改善,基因疗法治疗SCID-X1似乎很成功。
2002年Fischer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公开了参与临床试验的前五位儿童的治疗情况:该疗法疗效显著,且没有明显副作用。确实如此,由于不存在免疫排斥反应,表面上看基因疗法似乎比骨髓移植的安全性要高很多。然而仅仅在文章发表几个月之后,接受Fischer治疗的一位男孩就被确诊患有白血病。截至2005年,接受Fischer治疗的病人中有5位被诊断患有白血病,其中有一位因治疗失败不幸去世。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Jesse的死亡和5名儿童的白血病?原因在于基因疗法所使用的病毒载体。
其实将外源基因引入人体细胞的方法很多,比如使用电击在细胞膜表面穿孔使DNA分子能够进入细胞内部,或者使用脂质体递送DNA。但这些方法在需要大批量细胞操作的时候效率太低,所以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借助病毒的力量将具有正常功能的DNA递送至细胞内。
类似莫罗尼小鼠白血病病毒 (MoMLV) 的逆转录病毒病毒可以识别特定的细胞,在与细胞表面受体结合之后病毒可以将自身的蛋白质和RNA注入宿主细胞。RNA经过逆转录生成DNA后该DNA会被插入到宿主细胞的基因组之中。如果逆转录病毒携带具有正常功能的人DNA (病毒必须经过改造,比如去除壳蛋白),并将其插入到人宿主细胞的基因组之中的话,这些经过基因改造的宿主细胞就能够表达该DNA,生成相应的蛋白。
病毒载体相比物理DNA递送方法要高效很多,但科学家们没有预料到的是,虽然已经对病毒进行改造使他们无法再体内复制,但这些病毒的破坏力仍然没有消除。Jesse在临床试验的过程中使用的是一种重组腺病毒载体,虽然经过减活,但注射之后仍然引发了强烈免疫反应并导致了他的死亡。医生们推测Jesse在此前曾经感染过类似病毒,因此他体内的免疫系统对同类病毒的免疫反应更加强烈。这也解释了为何在18名接受一期临床试验的患者中只有他不幸去世。
所以,这些结构简单的病毒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容易控制。我们不仅很难控制某一些病毒在人体内的引发的免疫反应,最重要的是我们也难以控制该类病毒DNA插入人基因组的位点。如果病毒DNA插入负责人重要功能的基因之中,将有可能破坏这个基因的原有功能。同时如果病毒DNA插入特定位点也有可能激活附近的人体DNA。事实上Fischer临床试验中使用的MoMLV病毒正是因为插入了LMO2等基因上游并激活了附近的基因,使造血干细胞相关转录因子活化从而诱导生成白血病。
两场接踵而至的悲剧对整个基因治疗领域产生了极其沉重的打击。各国监管机构立刻采取行动,叫停了几乎所有正在进行的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之后科研人员也开始全面和冷静的分析之前的临床试验。2002年之后,医生们持续追踪当初接受基因治疗的十几名儿童的健康状况。5名罹患白血病的孩子中有一位不幸去世,其他4位在接受化疗后痊愈。而所有这些孩子,在10年后仍然非常健康。骨髓干细胞的进行基因改造,成功地治愈了他们的严重免疫缺陷。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安全性更高的病毒载体。在此之后科学家们改进了MoMLV病毒载体,使其影响人类基因正常功能的能力大大降低。与此同时,科学家们还把目光转向了逆转录病毒和腺病毒之外的其他病毒,比如慢病毒和腺相关病毒。
与MoMLV类似,慢病毒在侵染人类细胞后会将自身的遗传物质整个插入人类基因组DNA。但是慢病毒DNA插入基因组时不具有位点专一性,大大降低了慢病毒载体集中插入一个癌症相关的基因附近从而诱发癌症的风险。从2009年第一个基于慢病毒的基因疗法之后,已经有超过300个临床试验使用了慢病毒载体。而且截至目前使用该类病毒载体接受治疗的患者中无一例癌症产生。
尽管慢病毒的体外 (ex vivo) DNA递送效率很高,但该类病毒载体在应用于体内 (in vivo) DNA递送的过程中会存在很多缺陷,比如体内分布性质较差,容易被血清中的补体中和等等。而腺相关病毒在体内应用方面存在很大优势。也正是这类病毒载体的使用修复了Corey的眼睛,使他看清了这个世界。
V
2008年9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费城动物园上空飘扬着五彩斑斓的热气球。8岁的Corey Haas抬头望向天空,刺眼的光线使他的眼睛感到一阵刺痛。而此时他的父母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Corey患有莱伯氏先天性黑蒙症 (LCA),该病是由遗传性RPE65基因突变导致的。RPE65在视网膜色素上皮中表达,参与视觉光信号传导通路并可将全反式视黄酯转换为11-顺视黄醇。因此RPE65基因缺陷可以干扰视觉光信号传到过程,引起视力障碍。与此同时,正常RPE65蛋白的缺失会使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逐渐死亡,如果这些细胞全部死亡的话即使使用基因疗法也无济于事。但这类细胞的死亡过程会持续数十年,因此在疾病早期使用基因疗法仍有可能恢复视力。
Corey出生后不久他的父母就发现他不会与人对视,而且眼球总是来回移动。六个月大的时候他的视力问题越来越严重,但医生以为这些问题只是由于Corey眼部发育迟缓导致的,因为除了眼部问题,Corey并没有出现其他异常。两岁的时候,医生终于确定他存在视力障碍,Corey眼睛虽然能够感光,但是却看不见东西。
由于医疗水平和基因检测技术的限制,直到Corey六岁的时候才最终确诊。Corey的父母对于他的确诊感到十分难过,因为对于LCA患者来说他们的视力水平会逐渐恶化,最终导致完全失明。当他们得知Corey有资格参加基因疗法的临床试验时,他们没有犹豫,决定拼尽全力治疗Corey的眼睛。
2008年9月25日,Corey在费城儿童医院接受了治疗。医生将480亿个携带RPE65基因的病毒注入了Corey的左眼。仅在短短4天之后,当Corey站在费城动物园门口的时候,阳光射入Corey的眼睛,这个世界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Corey眼前展开。
其实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基因疗法的治疗领域早已从早期的单基因遗传病扩展到其他疾病,而癌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实际上美国批准的第一个基因疗法临床试验的应用领域正是癌症的治疗。1988年RAC批准了Rosenberg的临床试验申请,使用基因标记追踪癌症患者体内的TIL细胞。Rosenberg发现TIL/重组IL-2联用对于部分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有效,而在该临床试验中Rosenberg使用基因标记 (NeoR基因) 对TIL细胞在体内的分布以及生存时间进行追踪,发现TIL细胞会影响注射位点的黑色素瘤细胞的生长。
截止目前癌症仍然是基因疗法应用最广泛的领域,而且相对而言肿瘤领域的进展比遗传病领域要迅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第一个基因疗法产品的上市地点不是在美国,也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中国。2003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批准了全世界第一款基因疗法产品今又生 (Gendicine) 。今又生是一款携带p53抑癌基因的腺病毒载体基因疗法产品,用于头颈部癌的治疗。在2005年,SFDA批准了全球第二款基因疗法产品安柯瑞 (Oncorine),这也是全球第一款批准上市的溶瘤病毒。然而由于当时国内的新药研发正处于独特的历史发展时期,国际上对于这两款产品的临床试验数据以及真实世界应用的疗效存在巨大争议 (Science. 2006, 314:1232-1235),因此在上市几年之后便消失在了西方世界的科研工作者的视野之内。2007年,菲律宾食药监局批准了全世界第三款基因疗法产品Rexin-G用于治疗实体瘤,然而这些产品的疗效非常有限,并没有对肿瘤的治疗产生革命性影响,直到CAR-T疗法的出现。

已批准上市的基因疗法产品
VI
85%的ALL儿童患者在经历两年的标准化疗之后可以被治愈,但有15%的患者即使使用最高强度的化疗方案也依然无法缓解病情。一开始Emily的医生以为她患的只是普通的白血病,但在疾病复发之后医生意识到她的ALL并没那么容易治疗。
Emily的父母对她下一步治疗方案的制定感到万分忧虑,他们决定咨询其他医生的意见。而费城儿童医院的Rheingold医生给出的治疗建议与Emily当时的主治医生一致:希望Emily能够进行下一轮更高强度的化疗。但Rheingold医生同时也说,如果他们想选择其他治疗方案的话她也能够帮助他们。
Emily的父母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进行了化疗。但仅仅4个月之后Emily就出现第二次复发,并且病情迅速恶化。此时Emily的父母意识到他们必须更换主治医生,并寻找不同于普通化疗的、更加前沿的治疗手段。在确定无法进行骨髓移植之后费城儿童医院给出的建议是参加一项CAR-T疗法的临床试验。该疗法需要对T细胞进行基因改造使其能够识别CD19,在体外培养完成的T细胞回输至体内之后使这些T细胞能够识别B细胞表面的CD19,从而引发杀灭癌变B细胞的免疫反应。
在此之前已有3位成年病人被招募进入该临床试验,而且这几位患者对该疗法的响应非常好。但儿童患者对CAR-T疗法的效果如何却没有人知道。在与费城儿童医院的Rheingold和Stephan Grupp医生交流之后Emily的父母决定冒险让她参与该临床试验。如果这一次不成功,Emily大概就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了。
4周之后Emily的T细胞制备完毕。2012年4月17日,Emily成为第一个接受T细胞疗法治疗的儿科患者。Grupp医生计划分三次将CAR-T细胞输入她体内。在初次输入10%的T细胞之后的第二天Emily接受了第二次治疗,这一次医生向她体内输入了30%的CAR-T细胞。
Grupp医生说在回输T细胞的几天后Emily可能会产生类似流感的症状,之前的三位病人也产生了同样的反应。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Emily的症状却比医生预想的要严重的多。
2012年4月18日,Emily接受了第二次治疗之后在父母的陪伴下开心的回到家中。晚上的时候Emily的心情特别好,还一直缠着她父亲Tom,想骑在他背上玩骑大马。但到了半夜,Emily忽然开始发烧。她的父母迅速将她送到费城儿童医院的急诊。之后医院迅速召集了多名医生机体会诊,而此时Tom站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女儿手腕、大腿动脉以及颈动脉被切开,并插入17根IV管以维持她的生命。
医生对Emily的父母说他们从未见过并且如此病重的病人,Emily大概挺不过这一晚了。虽然他们很清楚Emily的病情是由输入的T细胞导致的,但并不清楚她的体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Emily的妈妈坐在她的床边,安静的看着床边的呼吸机,她坚信不可能就这样结束,绝不可能。
此时Carl June的医护团队也没有放弃,加紧进行另一次血液检查以明确Emily体内的免疫反应。检查结果令医生们感到非常诧异,Emily体内的IL-6高出正常值近一千倍。医生们推测IL-6正是导致Emily病情如此严重的原因。幸运的是Carl知道如何应对,他的女儿因患有类风湿正在使用一款IL-6抑制剂tocilizumab。虽然tocilizumab从未被用于癌症患者的治疗,疗效和安全性难以保证,但即使用了tocilizumab,Emily的病情也没办法更糟糕了。
在Emily的治疗过程中,确实有极大的运气和偶然因素存在。在Grupp给Emily使用了tocilizumab之后,Emily的反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ICU的医护人员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病重的人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快速恢复,几个小时内Emily的病情便迅速缓解。

Emily whitehead
一周之后Emily在她7岁生日的那天醒来。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为她唱起了生日快乐歌。虽然闯过了鬼门关,但医生们依然不知道回输的T细胞是不是能够对她的癌症产生作用。
3周之后,医生们对Emily进行了骨髓检查,结果是阴性,Emily的白血病消失了。Grupp医生说,是CAR-T疗法救了Emily,但同时Emily也拯救了CAR-T疗法,如果Emily去世的话大概CAR-T疗法也不会存在了。直到现在Emily的ALL依然没有复发。2015年1月27日,Emily的父母与Emily共同成立了Emily Whitehead基金以支持儿科癌症的研究。
VII
其实基因疗法的魔力远不止于此。可能有的读者已经注意到无论是CAR-T疗法还是ADA-SCID的基因治疗都是通过向人体细胞中引入外源DNA片段来实现的。通过引入功能性DNA片段,并在体内生成相应的功能性蛋白来实现治疗目的。但是有一些疾病是由于某些蛋白的功能而诱发的,而非蛋白的正常功能缺失导致的。比如人T细胞表面的CCR5可以作为HIV病毒进攻T细胞时的辅助受体,而存在纯合子CCR5 delta32突变的人由于HIV进入T细胞的能力被削弱,使携带该类突变的人感染HIV的风险极低。因此修饰CCR5基因使其形成CCR5 delta32突变也成为了HIV/艾滋病治愈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然而这种基因修饰是无法通过引入外源DNA片段来完成的。过去近二十年来以来以核酸酶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蓬勃发展,比起传统的同源重组技术,该类技术不仅更加高效而且操作更加灵活。该类基因编辑技术包括ZFN,TALEN以及近几年大火的CRISPR技术。笔者之前曾经写过两万字长文对该领域最前沿的CRISPR技术进行介绍,并对疾病治疗领域的应用进行了详细解释 ,相信各位读者读完这一系列文章会对该领域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
由于基因疗法产品的特殊性,其制备过程非常复杂,因此其价格也极其昂贵。2012年EMA批准Glybera上市用于治疗一种极其罕见的遗传性脂蛋白脂酶缺乏症。这款药物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贵的药物,价格大约为100万美元 (根据患者体重该价格会有所变化)。由于Glybera价格太过昂贵,而且有效性研究也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在上市之后只有一位病人使用过该产品。2017年初UniQure宣布将glybera撤市。
去年EMA批准了另一款基因疗法产品Strimvelis,用于治疗腺苷脱氨酶缺乏引起的重症联合免疫缺陷。Strimvelis定价为66万5千美元,而且采取的是无效退款的支付方式。与遗传性脂蛋白脂酶缺乏症类似,ADA-SCID也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遗传病。每年欧洲大约只有十几位新生儿会患有该疾病,即使全部新生儿都接受治疗每年的销售额也只有大约八百万美元。尽管Strimvelis的价格比Glybera低很多,但真正选择使用该药物的病人却同样非常少,直到今年5月份Strimvelis才迎来了上市以来的第一位病人。
由于CAR-T疗法的适应症人群更广,公众对于该类产品的定价也更为关心。诺华在Kymriah今年8月被批准上市之后宣布其单次治疗的价格为47万5千美元,而Kite给新上市的Yescarta的定价是37万3千美元。
很多医疗方法和技术需要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才能保证足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人类第一次骨髓移植是1957年,但直到20年后骨髓移植手术的病人存活率才超过百分之一。1978年免疫抑制类药物出现以后存活率才显著提升。基因疗法也是如此,从1990年Ashanti治疗的初步有效性验证,到1999年Jesse的生物技术之死,以及后来五位由基因疗法引发白血病的儿童,再到2008年Corey视力恢复,以及2012年Emily的死里逃生,基因疗法从挫折中一路走来,才出现了医学上奇迹。
有时候觉得化学实验室的工作很枯燥,不知何时才能够找到一个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以至于有一天忍不住跑去问我的导师BK: How my chemical reactions benifit the patients?
也许有时候会陷入低谷,也许有时候会遭遇挫折,也许会觉得一直看不到希望,但或许走到最后你会感谢自己之前没有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