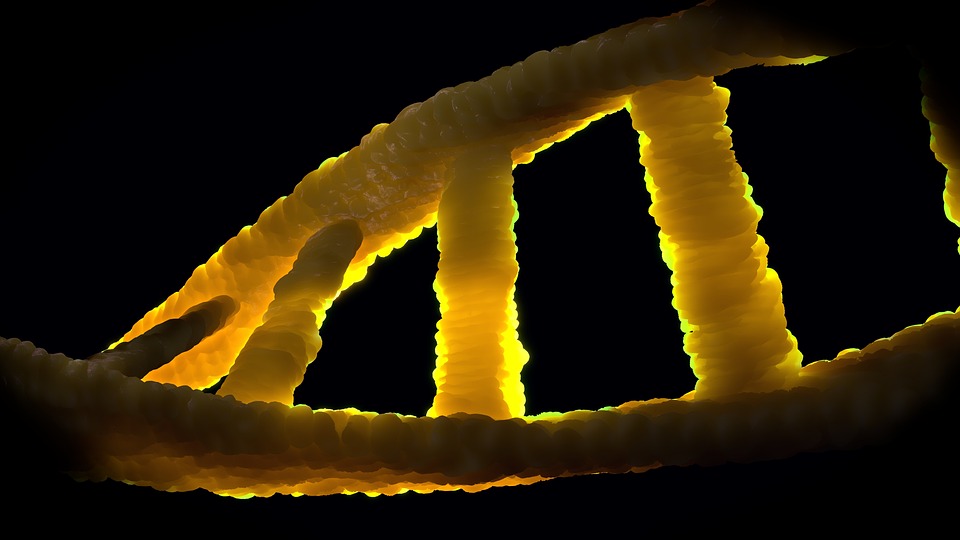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

2010年8月22日,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钟扬为观众讲述了基因组中隐藏的秘密。高剑平澎湃新闻资料图
他在16年间遍访青藏高原上的植物,收集种子送上“诺亚方舟”,并找到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拟南芥;他破解了红树北移难题,为50年后的上海送上一条“美丽的海岸线”。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钟扬教授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经过几十年的资源消耗,今后我们能给子孙后代留点什么?”给未来留下“种子”,贯穿他学术生涯的始终,引领他在世界屋脊上的奔走,直到被车祸戛然打断。
9月25日上午,钟扬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
“这个种子实际上是应对全球的变化。你猜测一下,假设一百多年以后还有癌症,假设那时候大家发现有一种植物有抗癌作用,然而由于气候的变化,这个植物在西藏已经没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个姓钟的教授好像采过了。”钟扬曾在演讲中说道。
“都一百多年了,姓不姓钟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教授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问我,我们的孩子如果采了这些种子能考上大学吗?一百多年过去了,没有人在乎你是不是教授。”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网站显示,钟扬1964年出生,1979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84年毕业于该校无线电电子学系。日本国立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生物系统科学博士。1984-1999年在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1996年起任研究员),其间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和密西根州立大学合作研究4年。2000年起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进化生物学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植物分子进化和生物信息学研究。2009年被教育部批准为长江计划特聘教授(西藏大学),中组部第六批援藏干部。
就在上个月,钟扬在“一席”上讲述了他与种子的故事。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作为植物学家,我们经常在讲,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钟扬以此开场。他以新西兰从中国“偷”了20多根猕猴桃枝条,把猕猴桃培养成第一大产业的故事,说明了种子的重要性。
“种种这些迹象表明,如果我们能获得种子,对我们的未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这些种子可以为我们提供水果,可以为我们提供花卉,改善我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有粮食作物。还有比它更重要的吗?还有,那就是医药。”
然而,种子们正在面临现实的威胁:“非常糟糕的是,由于全球环境的破坏,人类活动的剧烈,在了解和知道它能否被利用之前,它就已经没有了。怎么办?很多科学家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2000年新的世纪到来以后,科学家终于决定把这些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想法付诸实现。世界上目前最引人注目的种子库是斯瓦尔巴特种子库,我们称之为种子方舟或末日种子库。”
钟扬则与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合作,呼吁建议中国建立自己的种子库。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英国馆就是由邱园的科学家设计的。其中很多种子,是由包括钟扬在内的中国科学家提供的。
2004年,中国科学院在昆明主导建立了中国西南野生生物资源库。“这个种子库从数量上来说,至少在我国,在亚洲肯定是第一大,也是世界上并列的三大种子库之一。”
“吃”完8000个光核桃
钟扬选择的工作地点是青藏高原。据估计,青藏高原一共有将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其中有1000个是特有种。而从钟扬的实际见闻来看,这个数字是被严重低估的。
“我从武汉调到复旦大学工作,但是我发现上海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排名倒数第一,北京排名倒数第二。在这个两个生物多样性相对贫乏的地区,集中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差不多一半的人才。后来我申请了援藏。”
收集种子听上去可能非常浪漫,但其实过程中充满了许多艰难、甚至哭笑不得的故事。钟扬回忆了一种令人头疼的种子:光核桃。
“我们所有的桃子中间那个核是皱皱巴巴的,有皱纹,而它没有,是光的。这个桃子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目前查来查去,大概它最大的用处就是藏药里面有少许的用途吧。但是我们需要它,也许它就像猕猴桃一样,多少年以后它终于可以跟我们的水蜜桃杂交了。
杂交完以后显然我们想它有什么优点呢?水蜜桃很好吃,那它有什么优点呢?它抗虫、抗病、抗旱、抗寒。所有这样的优点,我们就可以通过非转基因的方式,经过杂交,再加上自然选择,来获得一种新型的桃子品种。所以我们知道潜在的意义是很大的,在潜在意义没有兑现之前,要紧的是先把它收集起来。
一个桃子里面有多少种子呢?一个里面一颗。所以我先收集8000颗,8000个桃子,装了两大麻袋,把它运回拉萨放在我的实验室里面。
如何把里面的种子取出来成了一个关键。如果有自动化方式就非常好,但是没有,也没有合适的尺寸。所以我就摆在门口,铺了一个台子,所有路过的汉族、藏族、老师、学生,每个人必须尝一尝。
尝多少呢?7颗。我们认为如果超过了10颗,很多同志一辈子都不想再见我了。这7颗拿了以后,他们都非常淳朴,特别是藏族朋友,一边吃一边呸呸,然后告诉我这个东西不能吃。他们说:老师,你采错了,它真的不能吃,而且很不好吃。
确实,我也知道不好吃,因为它以前就是猴子吃的。可是我们必须这样把它吃完,用牙刷好好地把边给刷干净,刷完了以后用布把它擦干,擦干以后必须晾干,因为不能暴晒,暴晒以后种子质量就会坏。”
收集8000个桃子,也绝非逮住一片桃林“薅羊毛”。考虑到遗传间的杂交问题,两个样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得小于50公里。因此,钟扬一天要走800公里。
“那个地方是高原,培养人特别慢”
尽管如此,钟扬每年都以“浪漫”的故事版本来吸引新的学生:“我每次做招生宣传都欢迎年轻的孩子们读植物学。我都讲请你们报考复旦大学或者西藏大学植物学,这好像是我们八项规定以后比较少有的公费旅游的专业。大概能跟我们专业媲美的也只有烹饪系,他们还可以公款吃喝。”
援藏16年,除了收集植物种子,钟扬还在西藏大学这个“世界最高学府”留下了其他“种子”。
“我说那个地方是高原,特别的慢,培养人特别慢。今年我的第五位博士德吉毕业了,藏族博士,也是我培养的七个少数民族博士中新近毕业的一名。
我在复旦大学可以培养很多博士,但是他们不一定对我们刚才所说的种子,或者像这样高劳动强度的、低回报的工作真的有那么大帮助。但是在西藏,我培养的藏族博士,他们毕业以后,至少这五个里面有四个都留在了西藏大学,都在西藏工作。”
“这是我们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在“一席”的演讲中,钟扬曾经介绍道,在7年时间里,他的团队收集了大约1000个物种,占到西藏物种的1/5。从今年起,他们要在墨脱开始新一轮的收集。
“如果这样,在未来的10年中,我们有可能再完成20%的任务。这样合在一起,我们大约能收集到超过西藏植物的1/3以上。我想如果我们这样的课题组都来做这样的工作的话,在未来的20年,我们有可能把西藏的高等植物收到75%。”钟扬说道。
西藏的植物种子们还会继续迎来收集和研究者,只是团队中不会再有钟扬的身影。就像50年后,当上海临港滩涂上的上千株红树苗蔚然成林,曾许愿在林中漫步的种树人也再不会出现了。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只有光秃秃的海岸线,不像美洲和澳洲著名的海滨城市,拥有美丽的红树林。2007年,钟扬课题组购买了10种红树庙12000株,种植在了上海临港地区一块荒凉的滩涂上,不幸全军覆没。人工栽种的红树林最北不过北纬27度,而上海地处北纬31度。温度和盐分,是两大考验。
钟扬团队在温室中逐步对红树苗进行抗寒训练,并从海里引水,使红树林的幼苗能够吸收到适量的盐分。
经历了近10年的千锤百炼,新一批千余株红树苗安然度过了上海2015年的冬天。“我的愿望是,50年甚至100年以后,上海的海滩也能长满繁盛的红树,人们提起上海的时候,会毫不吝啬地称其为‘美丽的海滨城市。虽然我看不到这一幕,但上海的红树林将造福子子孙孙,成为巨大的宝藏———这是我们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钟扬在2016年的开春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