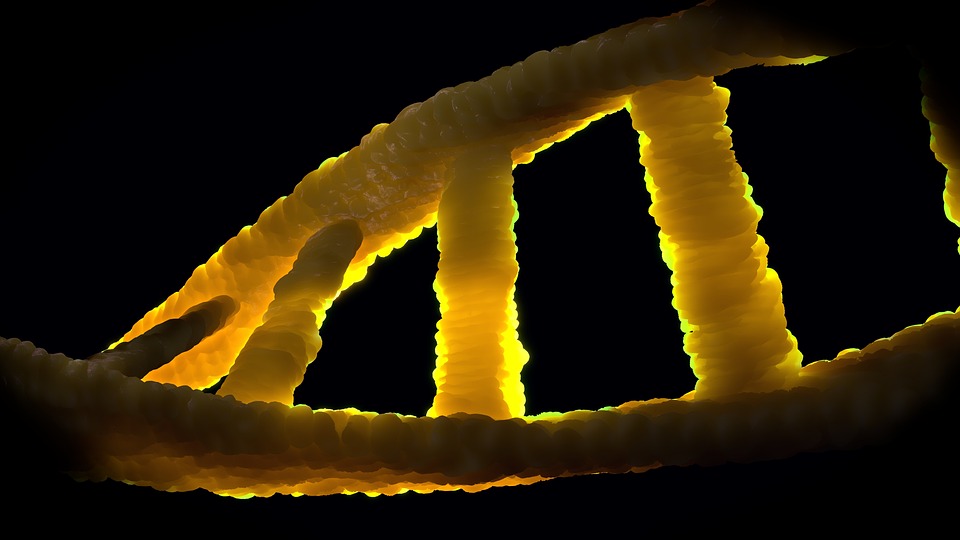对特定国家抱持科研偏见对建立良好国际关系所需的开放性是有害的。
今年4月,全球首名三亲婴儿健康降生。9月,执行这一临床操作的团队宣布,他们所使用的线粒体移植技术似乎让这名婴儿避免了线粒体遗传疾病。墨西哥新希望生殖医学中心的科学家和临床医师对这名婴儿在墨西哥诞生而感到骄傲。
但兴尽悲来,来自其它国家的科学家和伦理团体——他们曾花费大量时间起草这种医疗操作的指导原则——对这个意外声明回以批评。在采访和会议中,研究者和专家语焉不详地质疑新希望团队是否适当告知了病人相关情况,是否违反了法律,并提醒人们墨西哥有众多地下干细胞治疗诊所。他们的言下之意很明显:造就三亲婴儿的团队没有按章办事,而这里的章指的是这些专家所认可的规章。
新希望位于瓜达拉哈拉的诊所接受墨西哥联邦监管部门的质量审查;研究者表示,伦理审查委员会(IRB)也已经依据联邦法律批准了线粒体移植项目。“为什么英国的IRB就比我们墨西哥的好?”医学主任Alejandro Chávez-Badiola在采访中向《自然》发问。“这是科学沙文主义。”
平心而论,新希望诊所自身的行为也加剧了人们对它的不佳印象:一方面,它通过大众媒体和科学会议公开消息,而非在期刊上发表;另一方面,它还对研究缺乏审查做出了轻率的发言。的确,在美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下,这种操作是无法通过的。尽管如此,仅仅因为临床操作的执行地点而暗示研究有问题仍然是一种迂腐而有害的精英主义论调。
研究人员带着成见谈论其它国家科研的情况并不罕见。例如去年,当一群中国科学家首次编辑人体胚胎DNA时,这种成见便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大多数记者在采访时都会听到认为中国的伦理标准更低的傲慢评论。很难相信这些科学家不会在同事和其他人面前发表同样的评论。
回顾历史,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偏见。冷战时期,格鲁吉亚等国家在长达几十年内都无法获得抗生素。这些国家拥有关于噬菌体疗法(利用在环境中发现的病毒杀死细菌)效力的多年数据。这种疗法应该是可行的,但是美国和英国等一些国家的传染病专家却不愿意考虑噬菌体疗法的潜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使用的,而不是“现代”医学发现的。因此,传染病学界走上了固步自封的道路,甚至在面对严重的抗生素抗性时也是如此。
这种批评不会见诸期刊报端,它们暗中作怪,因此难以直接对抗。不过,它们也不一定是恶意或有意而为的。与任何微歧视一样,它们更可能被暗示出来,隐藏在意味深长的话语中——比如“毕竟是俄罗斯嘛”,也会出现在与同事的日常对话中,或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当作一种解释。要直接向这些言论发起挑战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模糊不清,只是在暗示“他们的做法和我们不一样”。
当然,任何单一群体的所作所为都不应脱离实际。研究者需要讨论是否应该在特定领域达成国际一致,比如不可违背的《赫尔辛基宣言》的人体试验规定。在要求来自任何国家的研究者对其研究的伦理和科学基础保持开放态度时,研究者也不应退缩。
但是,关于特定国家科研状况的明显成见会损害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有可能造成反弹。而且,采用科研本身的价值以外的因素来评估研究也是不科学的,可能会损害建立良好国际关系所需的开放性。
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因人而异。灵长类动物研究在多个欧洲国家受到法律限制,如果欧洲研究者和前往相关监管较松的国家进行人体胚胎研究的科学家一样,来到美国继续进行灵长类动物研究,评论者会攻击他们吗?
无论是好是坏,法律、伦理乃至科学标准都是一个相互交织的整体,而且很可能继续保持如此。为了适应这一点,许多期刊都要求作者遵守本人所在地区的法律和伦理标准。例如在美国,IRB会根据各州的法规等其它因素,逐例制定有关人体研究和动物研究的具体规定。
这个整体需要国际间的交流对话,以及对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开放态度,而成见和隐藏的偏见对此均毫无帮助。认识到存在哪些偏见——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的——然后考虑就所述研究而言这些偏见是否合理,是迈向公正评估科研成果的必需一步。
原文以Judge science on merit, not assumptions为标题发布在11月9日的《自然》社论版块
参考资料:
Nature:doi:10.1038/539139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