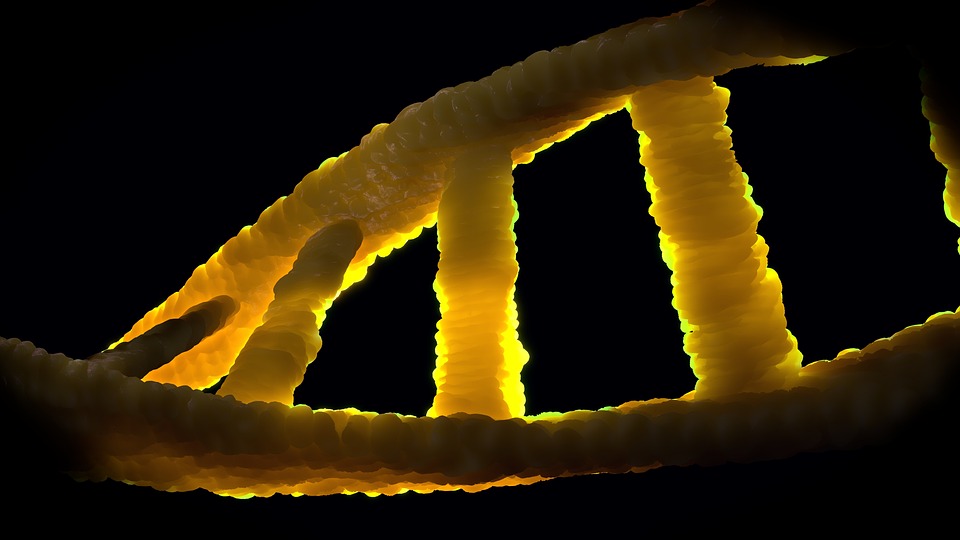2015年,我国科学家屠呦呦教授因青蒿素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重大事件。我们知道,青蒿素对付的是一种有致死危险的恶性传染病——疟疾。以青蒿素为代表的药物使人类在抗击疟疾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数据显示,就在青蒿素摘得诺奖的2015年,全球仍有2.14亿疟疾病例,其中死亡例数为43.8万。人类与疟疾等虫媒传染病的斗争尚未结束。
当前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虫媒疾病是登革热。登革热的全球发病率在近几十年来剧烈上升,至今已有大约半数的世界人口暴露于疾病风险之中。欧洲也存在登革热暴发的可能性,而重度登革热是许多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儿童住院和死亡的首要原因之一。据评估,每年有3.9亿人感染登革热。

除了使人直接遭受疾病痛苦之外,一些昆虫还威胁着人类的食品安全,增加了满足人们粮食需求的困难。虫害影响着粮食生产、储存、运输和使用等各个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农业损失,动物性的虫媒疾病也破坏着牲畜养殖业。面对人类感染虫媒疾病和虫害导致的粮食减产两大难题,人们将解决方案与问题的根源——昆虫联系了起来。
转基因昆虫技术起源于20世纪中期,它试图对病原性昆虫和农业害虫进行基因改造,将某些特定基因片段插入昆虫现有的DNA中,使昆虫原本的功能发生改变或降低昆虫的生命力,这样它们就不那么容易传播疾病或损害农作物。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转基因昆虫技术提供了两个思路,即所谓的种群抑制策略和种群替代策略。
种群抑制的目的是通过向昆虫引入致死基因,使其后代不能存活,从而减少害虫或感染虫媒的种群数量。实际做法是,先在实验室里通过转基因方法培养一批携带致死基因的雄性昆虫,随后释放至环境中与野生的雌性交配,这样产生的后代便无法存活,种群数量由于繁殖成功率的下降而减少。但由于致死基因只能传递一代(转基因雄虫的后代不能存活和进一步交配),且一只转基因雄虫由于寿命、环境等因素在其繁殖期内的交配机会是有限的,加上该策略是控制新增的繁殖数量而非直接减少种群的总体数量,因此为了快速控制虫害,往往需要向环境投放大量的转基因雄虫。种群替代策略对昆虫进行基因改造的目的是改变其天然性状,影响害虫的生理机能从而对农作物无害或者使感染虫媒不受到病原体的感染。该策略的修饰基因可以多次传代,且由于基因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们有可能突破自然遗传的规律,让昆虫将修饰基因稳定地传递给几乎所有的种群后代。
转基因昆虫技术容易与当下热议的转基因作物联系起来。尽管二者的技术实质相同,但就粮食作物对人类的影响来说,仍有一定区别。理论上,对害虫进行基因改造,而非直接以人们入口的粮食作物为目标,转移了基因改造风险的承担主体,或者,即同样在人—农作物—害虫等整个生态系统内增加了风险,但延长了风险传递的链条,分散了原来由人类承担的主要风险。这与将转基因的目标定位于玉米的叶子上以提高光合作用效率,而非直接让害虫食用致死的作物果实原理类似,即是风险转移。当然,只要引入了风险,就仍有可能通过基因突变等其他方式重新影响到人类,并且如同所有的抗虫害手段一样,转基因昆虫技术也有可能产生抗性。届时,除了对环境的影响,还有可能需要采取更大规模的措施来弥补这一漏洞,比如,杀虫效用更强但毒害更大的杀虫剂、更复杂的基因编辑技术等等,而这又可能带来进一步的影响。因此,需要基于受益和风险的考虑,对转基因昆虫技术进行科学的评价,并不断监测各种可能的不良后果。
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尤其是一贯以来建立在实验基础上,并以实验结果为价值判断导向的自然科学技术,转基因昆虫需要通过试验为自己正名。这项技术应当具备实验室评价的累积证据,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大规模的野外试验。2015年11月,科学家通过转基因昆虫技术成功使基因修饰的蚊子将病原抗性基因传递给几乎所有的后代,这为原虫抗性基因快速传递至整个蚊子种群提供了可能。2015年12月初,有研究表明,该技术的发展可以使蚊子的种群数量降至无法进行疟疾传播的水平。
全球唯一研发转基因昆虫技术的企业是发源于英国牛津大学的Oxitec公司,该公司已经在传播登革热的蚊子身上进行了野外试验,结果发现开曼群岛其目标种群数量减少至小于90%,这被认为足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防止登革热的流行。
目前,英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应基于上述科学证据和一些其他研究,批准并资助在英国本土进行一项大规模的野外试验,以进一步确定转基因昆虫技术在控制人类和牲畜传染病以及虫害方面的潜在效力。该公司的法规事务负责人卡米拉的发言谨慎又不失锋芒,她提到转基因昆虫技术的潜力,尤其谈到,英国拥有全球唯一一家研发该技术的公司,围绕技术展开政府咨询讨论,这体现出英国在该领域的世界领导地位,并表示如若英国愿意与该公司一道探索转基因昆虫技术在欧盟乃至世界范围的应用潜力,该公司愿意参与在英国进行的野外试验。
Oxitec公司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是,这家发源并根植于英国著名学府的生物技术公司,首次野外试验并非在英国本土或欧洲地区,而是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进行。这固然可以通过诸如开曼群岛这样相对狭小封闭的环境,巴西作为典型的传染病样本区域等原因来说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公司或监管者对转基因昆虫技术风险的审慎。无论如何,从累积的实验室证据和野外评价结果来看,我们有理由支持这样的试验在更多的地区进行。如同药物的临床试验那样,总有一批人会率先作为“试验品”,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们也可能是无药可医、有药难医窘境下的第一批受益者。
对于转基因生物的审批,英国和中国也都有一套可行的法规和流程,但现在转基因昆虫的新问题又摆在了眼前。转基因昆虫与转基因作物有些不同,它本身的流动性更强,这使得它不像农作物那样,可由特定的区域边界隔离。目前,全球没有一致公认的法规或条例来对转基因昆虫的试验或审批做出规定。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转基因蚊子试验的指南,但该指南只是对相关法规建立的更高层面的指导,指出一个法规管理框架需要包括个案评估、环境暴露、风险、受益等,并未涉及可操作性的技术指导。
转基因在中国的争论从未停止。回顾转基因作物在中国的历程,技术开发不透明、法规监管无公信力、公众未能有效参与是重要的原因,而非法种植的现象更让公众的抵触情绪进一步高涨。对于转基因作物,我们已经错过了以政府—研发者—民众良性互动模式进行发展的机会,而转基因昆虫技术使我们再次面对这样一个风口。现在,我们有机会开始建立从试验审批到风险评估的监管流程,并逐步扩大至核查和惩处措施,打造一个有公信力的监管体系,重塑公众对话。这么做是有价值的,因为从转基因作物到转基因昆虫,已为降低风险作出了建设性的尝试,而这些技术也在着眼于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不断迈进。
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如何不因利益驱动而招致试验结果的偏见,并诚实地将转基因昆虫作为众多途径中的一种。毕竟,就像对抗疟疾那样,人们也有可能找到类似青蒿素那样的有效药物,但在此之前,人们应该在有力的监管和科学性评估的基础上保持开放的心态,探索各种可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