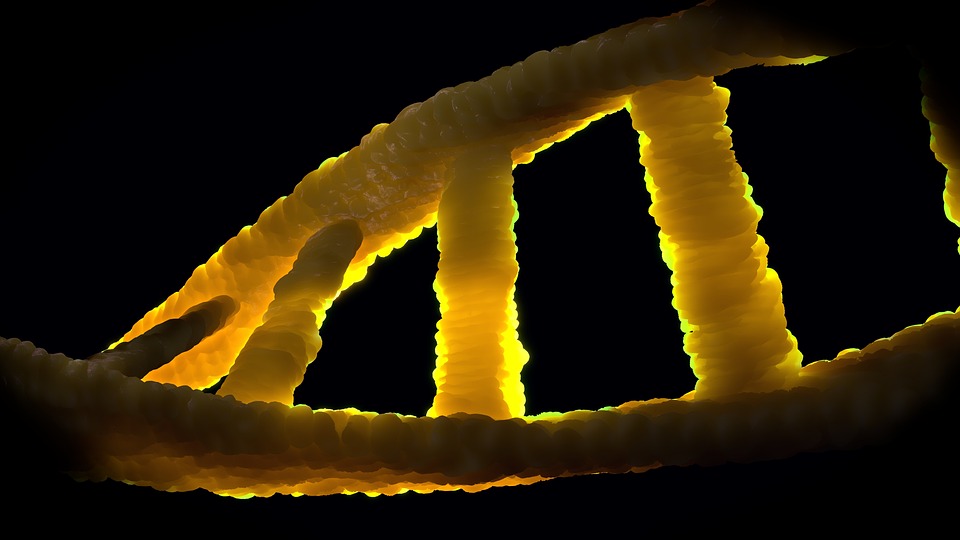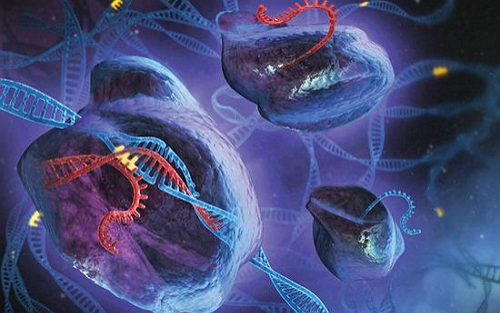
正在生物体内发挥功能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系统 插画:Stephen Dixon

电影《纳粹狂种》讲述一名纳粹军医用希特勒的细胞克隆出94个小希特勒,这正是科学家担心基因编辑被滥用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之一
几个月来,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造人类生殖细胞的科学研究陷入了伦理争议的漩涡,多家国际媒体先后发表文章,质疑这一技术可能带来的生物危害和伦理风险,并希望社会各界制定原则性框架并公开讨论。
近日,自然出版集团旗下最重要的子刊之一《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联系全球50位著名研究者、伦理学家和商业领袖,邀请他们对人类生殖细胞改造所引起的伦理争议等10个问题发表评论。最终,《自然·生物技术》收到了其中26位的回复,并刊载于5月12日在线出版的杂志上。回复几乎一边倒地认为,生殖细胞基因工程未来不可避免。
科学家一边倒地认为这一技术“不可避免”
参与这场大讨论的26位科学家来自全球顶尖大学和医药公司,包括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发明人之一艾曼纽·卡彭特(Emmanuelle Charpentier)教授、曾带领团队挑战“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生物学家克雷格·文特尔(J. Craig Venter)等。其中也不乏大家熟知的中外华人科学家,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张锋(Feng Zhang)博士、冯国平(Guoping Feng)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季维智( Weizhi Ji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李劲松(Jinsong Li)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周琪(Qi Zhou)等。
当前基因编辑技术、体外人工授精和生殖干细胞研究的发展速度已经大大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尽管遭遇伦理争议,但大多数受访科学家(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教授、生物伦理学家R. Alta Charo、英国克里克研究所研究员Robin Lovell-Badge等)几乎一边倒地认为,生殖细胞基因工程未来不可避免。
如美国爱迪塔斯医药公司(Editas Medicine)CEO卡特琳·博斯(Katrine Bosley)就认为,“人类生殖细胞工程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只是我们至今还没有深入思考如何管理或监管它,因为直到现在它还是个相当理论性的东西。通常情况下,技术上的某个突破会迫使我们快速面对复杂的问题。但我有信心,我们会经过深思熟虑后慎重使用它——在技术诞生早期就对它加以讨论,说明了科学界看到了它可能产生的后果,也看到了将这场对话范围扩展到基因编辑领域以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让讨论不局限于科学家和临床医生。每个人都有参与讨论的权利,还有很多不同角度的意见需要成为讨论的一部分。”卡特琳·博斯认为,我们有责任找到正确的方法实现这一强大技术的潜力,也有责任在使用时高度符合伦理。
美国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主席、生物学家克雷格·文特尔也指出,“基本上没有有效方法可以监管或控制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生殖系统中的使用。我们这个物种,将不惜一切代价去试图提高在我们看来好的性状,除去疾病风险或从未来后代身上移除我们认为差的性状,特别对那些有办法或机会接触到编辑技术和生殖技术的人来说。问题是何时做,而非是否会做。”
给个人健康和社会带来哪些利弊?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会面临一些潜在风险。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表示,脱靶效应以及基因嵌合现象是目前可以预见到的风险。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发明人之一Jennifer Dounda认为,尽管基因编辑的脱靶发生的可能性能够最小化,但是重要的基因仍有可能发生变异。男性细胞中,X染色体上基因只有一份,并且是从其母亲那里遗传过来,因此突变会带来更高的风险。而且如果“编辑”的基因改变并不完全,仅仅被改变了一部分(嵌合现象),在重要组织中仍然可能会出现病变细胞。此外,导致疾病的基因突变可能已经将生物体的遗传背景改变,而这将使疾病突变变为野生型基因,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
不过,正如路易吉·纳蒂尼所言,生殖细胞基因工程对健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能节省花费在慢性疾病和残障患者身上的医疗系统开支。”英国巴斯大学哺乳动物分子胚胎实验室研究员安东尼·佩里(Anthony Perry)也指出,3000多种单基因遗传性疾病性状有很多可以被消除掉。
相对于个人健康风险,社会风险更引人注目,争议也更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伦理学教授乔纳森·莫雷诺(Jonathan Moreno)认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还有‘消费者优生学’现象,即由父母的选择、而非国家命令所驱动的优生学行为,而这会产生和传统优生学类似的结果,如基于基因优化产生的社会阶层分化。在非常遥远的未来,有些国家也许会希望制造出具有超能力的个体作为士兵。我说的是《纳粹狂种》的情节。”
路易吉·纳蒂尼则持相反意见:“某些夸大其词、但却有广泛影响的观点认为,基因编辑技术会导致科幻小说的情节出现:人类依靠设计进行繁殖,引发一系列无法预料的结果。这些想象中的情节本身没有现实性,而且会引起社会对科学家的恐惧和不信任,同时使得对当前技术的应用过度谨慎。而这可能会妨碍科学家们全面开发更富有成效的体细胞基因治疗、生物技术以及生物医学应用。”
纳蒂尼指出,科学家应该约束(自己不去)描绘那些不切实际但却传播甚广的人类基因组编辑工程的应用。另一方面,为了帮助人们建立对科学和开放型社会自我纠错能力的信心,应该针对相关技术和应用的利弊进行公开讨论,并努力在科学团体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形成共识。特别是科学实验或生物医学干预中,哪些是可接受的,哪些已经超越了目前可接受的(实际操作和伦理)极限。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季维智则认为,不仅仅是生殖细胞,在所有类型的人体细胞中进行基因编辑都会引发一些社会挑战。首先,如果基因编辑费用高昂,只有富人能够承担得起,那么就意味着只有在那些最富有的国家才能接触到这些改良基因,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拥有“少生病”的孩子和“更加漂亮和聪明”的宝宝。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基因编辑技术可能会阻碍人类群体中的自然选择,对人类基因库中遗传变异的多样性造成意想不到的影响。第三,毫无疑问,这项技术将能够改善医疗条件并延长人类寿命。而如何处理这些进步对(社会)资源的消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在季维智看来,(基因编辑)最大的潜在社会效益就是帮助人类社会摆脱一些造成巨大痛苦并消耗大量资源的遗传疾病。
什么情况下才符合伦理标准?
受访科学家一致将安全性作为生殖细胞基因工程伦理上可行的第一标准,此外就是不能改变未来人类的“基本特征”。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亨利·格里利(Henry Greely)指出,“如果能被证明确实安全,我觉得能够最符合伦理要求的情况是,一对夫妇无法通过其他任何方式获得一个健康的、并且确实在生物学意义上属于他们的宝宝。”
Robin Lovell-Badge认为,只有修改生殖细胞是安全的时候,它才能在伦理上被接受。如果它是安全的,那么我,或许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可能都不会反对使用这项技术来避免遗传疾病的发生,特别是那些无法在人工授精卵植入子宫前进行遗传筛查的严重遗传疾病。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医学中心医学伦理学助理教授Annelien Bredenoord除了坚持要保证安全之外,还提出不能改变未来人类的“基本特征”。“我之前说过,生殖细胞编辑技术应用于临床,不能侵犯儿童享受开放的未来的权利。为了防止儿童被预先设定某种人生计划,看起来合理的办法是只允许基因修改扩大所谓的‘基本功能’。‘基本功能’是指对几乎所有人生计划都有用并且很重要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只允许对这样一些遗传性状进行修饰——它们对于孩子们未来所有的优质生活而言都是被需要的。” 对于目前基因改造生殖细胞的研究,最佳的监管方法是什么?是国际全面禁止、发布临时禁令、进行管控还是自由放任?受访科学家一致认为,临时禁令是可行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周琪表示,我们当前应该致力去解决一些技术问题,并通过动物实验去测试改造生殖细胞治疗的安全性和效率,但我们可以为未来应用生殖细胞改造来治愈一些严重的疾病敞开大门。
从实验室到临床还有哪些技术壁垒?
目前,生殖细胞改造仍停留在实验层面,即使如大多数科学家所言“不可避免”,从实验到临床应用仍然需要经历一段漫长的道路,需要突破诸多技术障碍。
意大利科学家路易吉·纳蒂尼(Luigi Naldini)认为,“改造生殖细胞,尤其是人类的生殖细胞,在应用中并不容易。首先,你得处理大量的胚胎,这样才有机会生成一些编辑过的细胞,这里并没有清晰的办法帮助识别和筛选那些被处理过的胚胎。另一方面,目前的胚胎筛选及移植策略将无法解决嵌合体的产生问题,而且目前还很难达到预期的效率。”
美国再生医学联盟主席爱德华·兰费尔(Edward Lanphier)也认为,获得高水平的特异性和通过高效的基因运输方法来减小目标器官发生嵌合现象(chemerism),这两点是临床应用中改变人类生殖细胞的主要技术壁垒。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李劲松研究员则认为,在生殖细胞介导的基因疗法应用于人类之前,至少还有三个需要解决的突出技术障碍,“以精原干细胞(SSCs)为例:首先,如何有效地诱导出一些人类生殖干细胞谱系;其次,是否有可能通过培养SSCs获得成熟精子;第三,是否可能实现对人类SSCs有效的遗传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