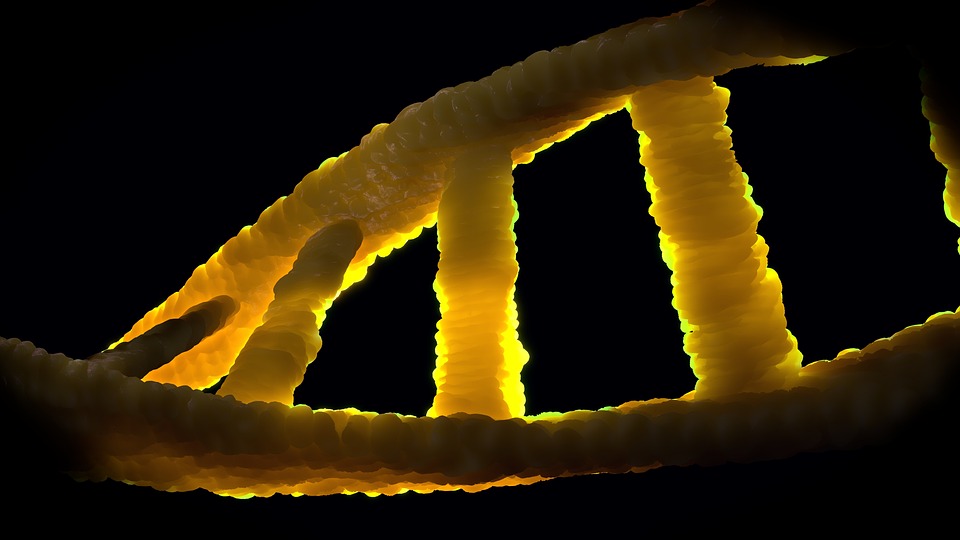转基因话题是公共舆论中的大热点,两边吵得一塌糊涂。我们可以试着套用马克思的句式来描述这一论争的发展态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挺转派”和“反转派”。
在既有的争论中,核心议题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这个议题当然重要,但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投到安全性上,就导致了对另一个同等重要的议题的忽视,即与转基因相联系着的知识产权议题,以及以知识产权为工具的资本扩张和积累。好比鸦片,我们记住了它对国民体质的伤害,但也别忘了,鸦片进口导致白银外流,给晚清的经济造成了摧毁性的打击。
让我们暂时搁置安全性的争论,来谈一谈转基因的政治经济学。
世界上丰富多样的物种属于谁?理论上,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但法律上,又是无主的领地。有人对自然物种的基因做了一下改动,便申请了专利,使之变为私产,要求使用者付费。
更有甚者,大农业公司还利用这个技术生产与种子配套的农药,挤出传统的物种,将农民锁定在其轨道上。好比一个软件公司,自己制造病毒,再开发杀毒软件卖给你。在软件业,这么干是犯罪,但在农业领域,还不是。
这样,农业成了资本更便捷地跑马圈地、积累增殖的领域。转基因已经给很多地区的农业带去了革命性的变化,但不都是好的变化。
这个变化得以成立,知识产权的逻辑在理论上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我们要分析知识产权理论在转基因领域的应用,也反思这种应用导致的伦理危机。很简单,知识产权越界了。
这一切背后的元推动力是资本,它组织起一个包括“官商科”的利益集团,裹挟舆论,通过钱的流行引导研究方向。它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做的事情与科学无关—对基因进行“修饰”(Modify)是一项技术而已。
它要改变世界,也正在改变世界。
明白到这一点,每个人都有权利对这种改变表达立场,愿意接受,或不愿意。
被转基因改变的世界
转基因食品问题在公共讨论中是一个关注度非常高的话题,在既有讨论中,最核心的关注点是安全与否。这一讨论足够热烈,以至于遮蔽了议题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转基因作物涉及的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以及更深层的资本积累问题。它关系到全球农业格局的重塑和世界上几十亿农民的身家生计,不能不予以足够的重视。
寡头垄断的种子市场
种子支撑着一个巨大的市场和产业。根据国际种子联盟(International Seed Federation,ISF)的估计,2006年全球商业化的种子市场规模为340亿美元,2012年增长到450亿美元。种子市场增长快的原因之一是种子的国际贸易快速增长,2005年国际种子贸易额不到45亿美元,2012年就增长到了100亿美元。
农作物的种子主要有三大来源:农民自留种、公共机构售种、私营企业售种。美国农业部2011年的一份报告(Research Investments and Market Structure in the Food Processing, Agricultural Input, and Biofuel Industries Worldwide)估计,2006年全球种子市场规模为290亿美元(比ISF的估计少),其中农民自留种总值61亿美元,占比为21%;公共机构售种为33亿美元,占比为11%;私营企业售种为196亿美元,占68%。在1995年(种子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三类种子的占比分别为25%、22%和53%,此后11年里,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赢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售种侵蚀了以公益为基础的公共机构售种份额,农民自留种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
种子市场“私有化”程度的上升,并没有带来竞争度的提高,相反,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局面。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报告,种子市场上规模最大的4家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在1994年为21.1%,2000年上升到32.5%,2009年达到53.9%。占市场份额最多的两家企业是美国的孟山都和杜邦。据一个叫ETC集团(ETC Group)的国际组织的计算,2011年孟山都的种子销售额为89.5亿美元,市场份额为26.0%;杜邦的种子销售额为62.6亿美元,市场份额为18.2%;排名第3的是瑞士的先正达,市场份额为9.2%。(ETC集团与美国农业部的计算口径不同,结果有些出入,但相差不大。)
美国农业部将孟山都、杜邦、先正达以及拜尔(总部在德国)、陶氏(总部在美国)、巴斯夫(总部在德国)合称为“六巨头”(Big Six),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农作物种子和农业化工两个领域都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和重要的市场地位。巴斯夫是化工巨头,目前种子销售额很小,但它对种子和生物科技的研发投入较多。根据ETC集团的计算,2011年“六巨头”在种子市场的份额高达60%。
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他们一般都是补贴的对象,与之相匹配的种子产业也应该利润较薄,需要补贴。但现实的种子产业与人们的印象截然不同,它现在是高度商业化、国际化、私有化、垄断性的产业,跨国巨头在这个市场攫取垄断利润。
种子产业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与农业化工联姻,“六巨头”都有种子和农业化工两方面的业务。这就是说,在跨国巨头眼中,培育种子和制造化工品具有相似性,他们用化工的思维培育种子。这是与人们将种子培育看作自然过程完全不同的思维。
转基因专利的冲击
种子市场在这十几年中的深刻变化,是由转基因专利引发的。
根据ISAAA(The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的一份报告(Global Review of the Field Testing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Transgenic Plants: 1986 to 1995),转基因食物第一次被允许用于商业销售是在1994年,美国批准一种转基因西红柿投放市场。1995年,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共批准了35个转基因农作物用于商业化种植。美国发放的许可最多,共有20个,孟山都有3种种子获得了许可,包括大名鼎鼎的抗农达大豆。1996年转基因作物开始在美国大量种植。从此,种子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
孟山都成立于1901年,从1940年到1990年,它的主要业务是化工。在生物科技方面,孟山都是后来者,1980年代才开始大规模投入,技术积累并不多。1995年之后的几年,孟山都收购了多家种子公司,这才在种子市场上确立优势地位。1997年和2000年,孟山都剥离了非农化工和医药业务,更加专注于种子和农业化工。2004年到2008年,孟山都又收购了一大批种子公司,成为了全球第一的种子公司。
孟山都在种子市场的统治地位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通过收购实现的。“六巨头”中其他几个公司的经历与孟山都相似,它们都在1995年之后收购了一大批种子公司,从而迅速获得大量市场份额,抢占寡头垄断的地位。显然,改变种子市场的不是科技的力量,而是资本的力量。
大资本为什么突然对种子市场感兴趣了?是转基因专利吸引了它们。
杂交等传统育种技术对于资本而言,不够有效率,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很长时间,不能迅速地获得利润。转基因技术大大加快了培育新品种的过程,在细菌上发现的抗除草剂基因,可以植入到玉米、大豆、土豆等多种农作物中,种子公司可以注册多项专利,销售多类种子,很快就能见到利润,而且可以长期受益。
世界是多样的,市场需求也具有多样性,生物更是多样的,但转基因技术及理念(如“实质等同”原则)消解了农作物的多样性,将农作物简化为几类物质和性状的组合。简化之后,跨国种子巨头只需要控制几类性状的供应,就可以在种子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现在,它们基本上控制了两种性状(转基因)—抗虫害和抗除草剂—的供应(部分得益于它们也是农业化工巨头,生产杀虫剂和除草剂),它们有这方面的专利,于是相当大一部分种子买卖逃不脱它们的手掌,要向它们缴纳大量专利费。不管种子多么有独特性,只要它含有抗虫害或抗除草剂的基因,种植者就要向它们付钱,否则可能被起诉。转基因专利使种子市场变得易于控制。
种子研发模式被改变
转基因专利不仅改变了种子市场,它还通过种子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其他方面,例如种子及生物科技的研发、农业的生产成本、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全球经济格局。
与种子市场私有化、垄断性相伴随的是种子研发的私有化、垄断性。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报告,在2006年全球农作物种子和生物科技的研发投入中,大型种子公司占75.6%,集中度非常高。种子研发的集中化也是从1995年前后开始的,1995年,种子和化工联合体(2002年之前,这样的联合体有十来家,经过一系列购并,2002年之后才只剩下“六巨头”)在种子和生物科技方面的研发投入占全球总投入的23%;而到2010年,“六巨头”的研发投入占到了全球的76%。
可以想见,种子研发的私有化程度也会比较高,但这方面的数据不多。美国农业部的报告仅计算了2000年食品和农业研发的结构,这一年,全球食品和农业研发投入为293亿美元,私营企业投入占45%;高收入国家食品和农业的研发投入为245亿美元,私营企业占50%;而在其他国家,私营企业仅占19%。报告没有计算近年种子研发中私营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比例。但考虑到高收入国家的示范效应和先发地位,以及这些年种子研发集中度的不断上升,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年种子研发的私有化程度也是不断上升的。
从研发取得的成果来看,私营企业要远多于公共部门。1982年到2007年间美国批准的农作物专利中,孟山都和杜邦分别占28.7%和36.5%,而公共部门和非盈利机构只占0.6%。在1985年到2008年,美国的转基因作物田间试验申请有39.7%来自于孟山都,来自公共部门和非盈利机构的只占26.4%。
显然,孟山都等跨国巨头主导了种子和生物科技的研发。研发是以牟利为导向的,而不是以科学和公益为目标。产品越赚钱,研发的力度就越大,与是否有利于人类或消费者无关。转基因种子是最赚钱的,于是就成为研发的主要方向;在转基因技术领域,抗虫害的和抗除草剂的品种最赚钱,理所当然获得最多的研发投入,产生出最多的研发成果。这本来是商业的逻辑,却往往被包装成科学的发展方向。
商业的要求使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小,从1995年转基因农作物被允许商业化到现在,抗虫害和抗除草剂一直都是转基因专利的主流,相比之下,其他方面的成果并不多。这对科技的发展当然是有害的,却有利于跨国种子巨头维持它们的垄断地位。垄断地位使它们能够主导研发,而对研发的主导又进一步加强了它们的垄断地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农民负担加重
跨国种子巨头垄断市场和研发的直接后果,是转基因种子的价格偏高而且涨得快,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农民不堪重负。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从1995年到2011年,每英亩大豆和玉米种植花在种子上的成本分别上升了325%和259%。美国一个非盈利组织有机中心(The Organic Center)在2009年12月发布了一份报告(The Magnitude and Impacts of the Biotech and Organic Seed Price Premium)提供了转基因种子价格的更多数据。根据这份报告,从1975年到2000年的25年间,美国大豆种子价格仅上升了63%;而在转基因大豆被广泛种植后,从2001年到2009年的8年间,种子价格上升了107%;传统种子的价格也随之上涨,涨幅为88%。2009年,转基因大豆种子的平均价格比传统种子高47%。2010年,孟山都的新品种抗农达二代大豆种子比抗农达大豆种子高42%,是传统种子价格的近两倍。玉米的情况也类似,2009年转基因玉米种子比传统种子贵69%;2010年,孟山都的新品种SmartStax的价格比原有转基因玉米种子的平均价格高30%~40%,是传统种子价格的两倍多。2010年,新品种的转基因棉花种子比传统棉花种子贵近6倍。
转基因种子价格高而且不断上涨(种子公司通过推出新品种从而涨价),也拉动了传统种子价格的上涨。有机中心的报告估算,1997年之前种子的成本只占大豆种植总收入的4%~8%,占大豆种植总成本的13%~23%;进入转基因时代后,传统种子的成本占大豆种植总收入的比例上升到8%~12%,占大豆种植总成本的19%~33%。种子成本占总成本的30%以上,占总收入的10%以上,这已经是很重的负担了。如果农民使用更贵的转基因种子,那种子成本就会占到总成本的40%~50%,占总收入的15%~20%。这是一般农户难以承受的重负。
在印度,一些农民没有足够的钱购买转基因棉花种子(比传统种子贵几倍),他们需要向银行贷款。如果当年雨水欠佳、收成不好,他们的收入无法偿还贷款,第二年就不能再贷款购买种子,而只能去借高利贷。如果第二年的收成仍然不好,很多人就会走投无路,一些人因此自杀。2002年,印度允许转基因棉花商业化,2005年之后,种植转基因棉花的农户迅速增长;2006年后,印度自杀农民的数量骤然增加。这两者之间是有一定相关性的。
摧毁农业生产
既然转基因种子贵得难以承受,为什么农民还会去购买?为什么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会快速增长呢?ISAAA认为,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从1996年的170万公顷增加到2013年的1.75亿公顷,增加了100倍以上,原因是它们给农民带来了收益,也反映了不愿冒险的农民对转基因的信心和信任。这种解释似是而非,至少是不全面的。
农民选择转基因种子的部分原因是,在一个寡头垄断的市场,他们的选择并不多。有研究发现,美国的非转基因种子从2005年的3226种减少为2010年的1062种,降幅为67%。农民会发现,他们熟悉的一些种子已经从市场上消失了,而转基因种子销量很大,似乎很受欢迎,值得信任。
转基因种子被选择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它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确实有人从种植转基因种子中获益,但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工业化的种植企业,这样的企业会选择转基因种子,而不是传统种子。
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是美国,位列第二和第三的是巴西和阿根廷。在这两个拉美国家,转基因种植面积的扩大伴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
阿根廷在1996年向孟山都的抗农达转基因大豆发放了许可,只比美国晚一年。当时的背景是,阿根廷面临资本外流、经济衰退的困境,大规模种植大豆用于出口可以创造外汇,这是阿根廷政府批准种植抗农达大豆的原因之一。几年之后,转基因大豆种子走私到了巴西与阿根廷邻近的地区。当时巴西是世界第二大大豆生产国,但一直禁止种植转基因大豆,但由于走私等因素,到2004年,巴西种植的大豆中已有20%以上是转基因大豆。2005年,巴西正式允许种植转基因大豆。
巴西和阿根廷的农场都很大,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下,需要雇用数量众多的农民。而除草剂农达和抗农达大豆的引进,以及免耕法的推广和农业机械的使用,大大减少了农场所需的劳动力。在免耕法的耕作模式下,农场并不整理土地,而是任由杂草和秸秆在地里腐烂;播种则靠专门的机器,将种子埋入杂草和秸秆之下的土地。据说这种模式可以改良土壤,它的缺点则是容易杂草丛生,如果人工除草,就仍需要大量劳动力,但使用除草剂则可能连农作物一起杀死。孟山都的农达和抗农达大豆解决了这个难题,农达可以杀死杂草,抗农达大豆却免受其害,那农场就只需要少数劳动力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机械化,转基因技术是使这种转变成为可能的条件之一。
这个转变伴随着大量农民失业,还有小规模农场经营者被大规模农场经营者挤垮,他们中的一些人涌入城市变成贫民。有人将这个过程与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相提并论,后者是“羊吃人”,前者是转基因技术驱逐农民。
从1995年到2006年,阿根廷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10%以上,即使在GDP增长率较高的年份也是如此;城市人口贫困率一度非常高。巴西也有类似情况,从2005年到2010年,农村人口加速减少,乡村人口贫困率一度非常高,失业率维持在8%上下。这些现象与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是有一定关系的。
转基因技术还改变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农业结构,大豆的种植面积大大增加,分别占总耕地面积的约40%和约60%。这两个国家和美国大量出口大豆,而中国则大量进口。这种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转基因技术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外,国际贸易量巨大的大豆等农产品(000061,股吧)作为大宗商品,其期货及其他相关金融产品成为国际金融市场 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全球的经济,牵动着巨大的利益—这远远大于种子市场的规模。
说到底,转基因专利对农业、科研、全球经济的改变,不过是资本逻辑的体现,转基因技术是资本实现其意志的便利工具。转基因技术在农业领域所催生的转变是非常巨大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倘若如国内的某些“挺转”人士所愿,中国也大规模推广转基因作物,不但农民原本就微薄的收入空间会被大幅挤压,作为中国发展缓冲地带的农村也可能会被重塑。这个代价—即便不考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也可能是中国所无法承受的。
认识孟山都
总部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孟山都公司,可谓转基因技术和产业领域的大哥大。在国内转基因研发推广和相关争论中,孟山都也是实际参与者之一。围绕着这家公司争议不断,去年和今年,连续发生针对孟山都的全球性抗议活动,抗议在52个国家的超过400个城市同时举行;但也有国内媒体组织报道,力证孟山都“不是黑心企业”,很多国家都受益于它的转基因技术。
对于这样一家公司,我们有必要有所了解,这对理解围绕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并非没有意义。不需做太深入的研究,仅根据公开资料就可以看到它的多重面目。
起家于化工
由约翰·奎恩伊在1901年创办的孟山都,1940年代的一个主要产品是滴滴涕,学名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DT)。孟山都是当时美国15家生产滴滴涕的厂商之一。虽然滴滴涕在灭杀蚊子抗击疟疾中曾经大显身手,但是它的毒性对其他生物的危害也逐步被认识到。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终于引发了抗议滴滴涕的环保风暴。环保运动经过10年抗争,美国环境保护署终于在1972年对滴滴涕下了禁令。
孟山都的另一项重要产品,是1920年代推出的多氯联苯(PCB),该产品曾广泛用于生产润滑材料、增塑剂、杀菌剂、热载体及变压器油。美国使用的多氯联苯,曾有99%出自孟山都。多氯联苯也是剧毒和高度致癌物质,在多氯联苯的污染遍及全世界,直至影响到南极的企鹅之后,美国国会于1979年禁止了它在美国的生产。
举世皆知的橙剂(一译为橘剂)则是孟山都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为美军生产的生物武器,用于越战。这种落叶剂以剧毒物质二噁英为基本成分,把掩藏越南游击队的茂密森林变成了光秃秃的山地。橙剂被国际癌症中心列为一级致癌物,可能诱发心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生殖系统紊乱和发育障碍,就连施放橙剂的美国大兵也有不少深受其害。
一个以剧毒物质为主打产品的化工企业,摇身一变成了以生物技术造福人类的公司,转变不可谓不大。孟山都当今的主打产品,一个是以草甘膦为基本成分的除草剂,另一个就是抗草甘膦的转基因玉米种子和转基因大豆种子。孟山都宣称,草甘膦除草剂和抗草甘膦的转基因种子都是无毒无害的,但是质疑者称,它当初推销滴滴涕时也是这样信誓旦旦的。如今,质疑这些产品有毒性的研究和报道已经越来越多。
强势压制批评
如果对孟山都的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还有争议,那么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这家公司面对批评和质疑时的强势。一位对孟山都无比景仰的前雇员也承认,孟山都“强势,霸道”。
暨南大学潘玢渠2009年的硕士论文《试析美国孟山都公司如何构建其在全球粮食市场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一文谈到了孟山都压制批评的手段,仅引一例:英国反转基因食品团体GenetiX Snowball采取非暴力行为,组织群众投入到制止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孟山都针对该团体的活动,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听证会上,孟山都寻求法院对这个团体下达永久禁令,并要求该团体提供所有接受其宣传册的人员名单以及住址。利用法律手段压制批评是大公司惯于采取的手段,小规模的社会组织或媒体由于无法承受漫长法律程序所带来的成本,一般不敢轻易进行批评,这使得大公司拥有更多免于监督的特权。
对于学术界的批评,孟山都打击的力度更大。不止一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质疑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论文在发表之后被撤稿,其背后都有孟山都的影子。
美国的南希·斯旺逊博士曾针对孟山都等大型生物技术公司批评说:“他们千方百计压制科学的调查。他们雇佣科学家,向学术机构提供金钱来资助科研。他们在各级政府的关键岗位安插人手;积极游说国会并利用其影响来胁迫别的国家接受他们的产品。他们往科研学术刊物安置主编,控制什么可以发表,而更重要的是,控制什么不可以发表;甚至到了只要他们认为坏了他们的事儿,就把已经发表的文章撤回的程度,从公开记录中抹掉这样的结果,为扩张铺路。”她还指出,有很多人在发表了怀疑基因工程的研究结果之后,被否定掉终身职位,失去了他们的经费甚至工作,这在科学界内部造成了一种恐惧的氛围。
背景雄厚
在美国政府和孟山都之间,那扇“旋转门”是通畅的,有多名要人曾先后在二者任职。
举例来说,米奇·坎特在加入孟山都董事会之前担任过美国贸易代表;威廉·鲁克尔斯豪斯在当上孟山都董事前先后担任过美国环保署(EPA)首任署长、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和司法部副部长;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1970年代在孟山都当过律师;孟山都前资深副总裁迈克尔·弗里德曼后来担任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副局长;琳达·菲舍先在美国环保署任助理署长,然后到孟山都当了5年副总裁,又回到美国环保署任副署长;迈克尔·泰勒曾先后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孟山都副总裁,目前任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高级顾问;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早年曾任一家名为西尔列的公司的CEO,任职期间该公司被孟山都收购,拉姆斯菲尔德个人的股票当时价值1200万美元。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就不一一列举了。
此外,孟山都与美国军方的互动也由来已久。早在1943年,当时执掌孟山都研发部门的查理斯·托马斯就应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之邀,参与了旨在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孟山都的中心研究部成了曼哈顿计划的签约研究单位,协助美国核武器的研发。托马斯1950年代和1960年代先后担任孟山都总裁和董事长。臭名昭著的橙剂就是孟山都根据美国军方在越战中的需要研制生产的。
华为公司被美国政府以安全原因拒之门外,理由之一便是任正非有过在中国军队服役的经历。在构建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下,哪怕仅仅根据对等原则,我们也要问,孟山都这样背景的公司是否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是否应当被允许进入中国呢?
曾就职英国皇家学院的分子生物学博士瑞卡达·斯坦布莱彻10年前对我说过,“科学家曾经被认为是中立的,非政治化的,所以被公众信任。但是在希特勒时代,德国所有的科学家都为纳粹服务。我们不能重复这个历史。现在有一个很危险的倾向,就是大家都要靠资金来做研究,而大部分资金是公司提供的。科研项目申请不再是为了社会的需要,而是为了如何拿到钱。很多资金资助只是为了应用的目的,是应用驱动的研究,也就是为了专利的目的。是专利激发的资助和研究。生物技术利益很大,公司吸引了很多科学家。但是科学家应该知道他们是容易被利用的。”
与孟山都相比,这样的科学家无权无势。但是她说,“我们会促使别人思考,也能阻止一些事。”
面对孟山都,我们难道不需要思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