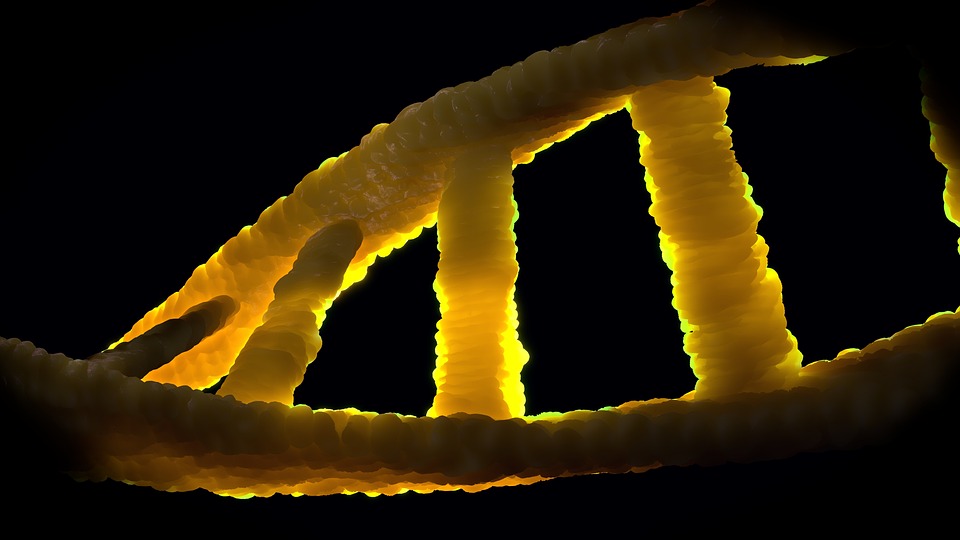转基因是近年来引人瞩目的公共话题之一,中间涌现出了多个传播事件,远远超越科学与农业的范畴,讨论之激烈、参与者之广泛、持续时间之长久都极为罕见。尽管至今为止,世界上所有主流科学机构都认为,当前的科学评估、生产实践都显示,转基因作物与常规作物一样安全,却仍不足以消除人们的疑虑。从传播学角度看,相关的传播受到了干扰或误解,舆论已经构建了非科学、非学术的表达框架,沟通失真导致了传播障碍。
仅用“新事物诞生必然遭遇接受障碍”这一规律,不足以解释转基因知识传播中碰到的问题。对转基因而言,科学术语的专业表达和公众所需要的通俗表达构成了两个话语体系,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信息流通通过语言这种“符号”来实现,“解码/编码”之间存在巨大偏差。
科学界和相关政府部门往往从科学知识的普及角度克服这些障碍。但实际上,转基因科学传播障碍的背后有着更为隐蔽的反智社会态度及对传统农业的迷恋心理,三个因素都与中国传统直观外推思维方式有关。
本文在梳理了天人观的历史脉络后,发现转基因知识传播所面临的,实际是构造自然观与有机自然观之间的冲突。对有机自然观的误读与当前弥漫的反智主义关系密切,转基因带有“高科技”的突出特征,恰恰容易成为反智主义攻击的对象。在有机自然观和“反智”传统的影响下,社会上对传统农业的迷恋有着相当的市场。但质疑现代生物技术、希望重返传统农业已经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转基因技术要克服传播障碍,必须重构环境,除了以经济动力继续推动传播工作外,也要让技术发展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自然观相结合。本文将分为追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反智的社会态度及对传统农业的迷恋心理三段来进行论述。
“天人合一”,有机自然观的误读
“虫子不吃人能吃吗”,一个简单的反问句式正在瓦解一批科学家数十年的努力。尽管从科学逻辑上看,这类言说完全经不住推敲,但却符合日常经验,能够调动公众的直观理解力,因而具有巨大的传播威力。动用常识来进行直观外推的简单句式之所以泛滥,依靠的是言说背后不易察觉的文化意义。
这个矛盾句式隐藏的回答是“虫子不吃人就不能吃”、“虫子能吃人才能吃”。由虫及人,暗含的逻辑是人与虫的同构。“虫子”是世界万物的一类,和人一样,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虫子”由此代表着“自然”。万物互相交感,人和代表自然的虫子能分享相同的食物,自然才是和谐的。虫子都不吃的转基因水稻,代表着“自然”的抗拒,而转基因水稻恰恰是科学家们(人)的创造。转基因的命运由此注定:它代表着人与自然的冲突,与传统的“天人合一”有机自然观格格不入。
在日常生活中,依赖于传统直观外推思维方式的有机自然观的影响随处可见。天然有机食物的热潮、吃哪补哪的食补法和各类荒诞不经的养生术,无不是“五千年文明”之花结出的奇异果实。转基因所创造的,恰恰是直观外推方式所不能理解的范畴。在这种思维方式及自然观里,任何打上“人造”烙印的物品都会受到审判。
转基因生物(食物)需要精确的基因克隆和转移,跨越了物种鸿沟,是完全意义的人造产品,如此“非天然”,肯定是“生而有罪”。不仅仅只有转基因食品,通过化肥、农药、植物激素得到的农产品,或者是运用食品添加剂的食物,它们也值得怀疑,不过程度不一而已。只有那些看起来更传统、天然的食品才更接近自然,因此更安全更好。正如田松等所言,“人类与水稻、麦子、玉米,都经过了漫长的适应过程,相互选择,相互改造,共同演化。人是环境的一部分,所以传统社会,一个人到达异乡,常常会感到水土不服——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食物都会不适,更何况是前所未有的人造生物!”
在“人造/自然”两者之间,“自然”似乎成了当然的选项。这不只是传统的幽灵,值得重视的是,“天人合一”有机自然观正在变得时髦。人们重提诞生于农耕文明时代的自然观,目的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希冀从传统中挖掘出有益于解决当前面临问题的价值。有学者认为,“天人合一”论已经达到了生态的高度,与今天所提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类似。
这种更相信直观经验,普遍接受万物互相交感,追求“天人合一”的有机自然观是如何演化而成的?在对待当下复杂问题时,这种自然观是否又能像提倡者所希望的那样,带来人与自然的大和谐?
“天”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最为悠久的一个哲学问题。直接将“天人关系”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认为“天人合一”是天人关系的精髓,概括历朝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和谐关系,这无疑是轻视了中国文化的复杂性。
首先是“天”的含义,历来就有多义。说“天”大致等同于如今统一完整的自然概念,不免牵强。《道德经?二十五章》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时的“天”和“自然”与今天的自然概念都相差甚远。
即使不纠缠于概念,中国历史上对“天人关系”的论述也是多样的,有“天人合一”、“天人相分”等多种观点。儒、道等诸子百家之间对“天人关系”的看法有显著区别,在人的能动性上,儒家相对积极。老庄“与天为一”的“顺天”说,荀子改造自然的“制天”说与《易传》的“天人调谐”说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天人合一”观,发源于周代,夹揉了老庄与《易传》,中间出现了孟子“性天相通”观点与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到宋代张载、二程时达到成熟。整体来说,“天人合一”自然观发展的各个阶段,无不强调人性即天道,认为自然规律和道德原则是一致的,无疑是过分强调人的内圣外王的精神体验而忽视了人对环境的现实需要以及所受的限制。
把追求道德完善视为人的最终价值判断的伦理中心主义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下意识,载其所支持的有机自然观下,对转基因这样“非自然”的产物,容易出现大量批评都集中在道德层面的现象,“研发者卖国、追逐利益,产品毒害国人”等阴谋论式的批评更能调动民众集体下意识,更具有煽动力。
在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实践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阐述天、地、人之间关系的“三才”理论。传统中国无疑是一个向土里讨生活的农业文明社会,其中发展起来的“天人观”,与“三才理论”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该理论是一种朴素的自然观和宇宙模式,更通俗地表述为天时、地利(或地宜)、人和(或人力)。“三才”中的天地人,最接近于现在所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先秦以来,“三才”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广泛应用到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处于人类之外的“他者”——天地,如何与人相处,二者如何在对立中寻求统一,顺应自然规律的同时,如何发挥人的能动性,这正是“三才”农学思想试图回答的问题。更为基础的“三才”理论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天地”的“他者”存在,进一步说明了“天人合一”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之不可得。
从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实际结果看,如果“天人观”中确实存在某种生态智慧的话,也只是停留在理想之中。自汉以来,中国环境整体持续恶化。余文涛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环境变迁的总趋势,自秦以降逐渐恶化。从先秦起,其间经历了良好-第一次恶化-相对恢复-第二次恶化-严重恶化等五个阶段,明清以后为中国环境急剧恶化时期,尽管造成环境整体趋恶化的因素复杂(最主要原因应是人口增长——编者注),但从结果上看,“天人合一”显然并未能调适人和自然的关系。
由此可见,和对转基因的争议一样,对“天人合一”现实意义的理解是有分歧的。可取的态度只能按“照着讲”的途径——即要尊重它实际的历史内容,才不至于陷入自说自话的怪圈。在如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古人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给出了异常丰富的回答,“天人合一”从来就不是唯一答案。如果不反思并完成“天人合一”有机自然观的现代转化,反而据此来反对转基因技术进而否定所有现代技术,恐怕只能是南柯一梦。
反智泛滥
“天人合一”并不等于“天人和谐”,这种有意无意的误读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前弥漫的反智主义。余英时说,“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
中国的反智论由来已久,儒学的法家化加深了“尊君卑臣”的格局,知识分子在政治化的道德中打滚,个人的命运和“才”(智性)都只是工具。在20世纪狂风骤雨式的革命中,科学家等知识分子被工农整体拒绝。后经拨乱反正虽稍有短暂春天,但又很快面临消费主义与世俗主义的狂飙突进,加上后现代主义浪潮的高涨,科学的价值被资本和权力消解,“反智主义”也获得了新的市场。
一般而言,“反智论”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一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的轻鄙乃至敌视。
和有机自然观一样,反智与中国人数千年来直观外推的思维方式直接相关。在常识和直观理解力所能及的范围,直观外推的思想方法比较接近科学,有着很强的实用性。一旦超越直观外推所能把握的领域,这种方式则很快滑入神秘境地,导致不可避免的反对智性和对知识分子的轻视。
作为典型的科学前沿事物,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符合人们想象的“高科技”:技术在肉眼不可及的微观层面展开,结果是快速改造和改变自然,所代表的新兴产业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点的诱人前景,商业化应用时间尚短。转基因的研发发展如此迅速,理解接受它显然不能依赖于常识和直观外推,需要相当的专门知识,此时,智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受到直观外推思维方式的影响,在转基因的传播过程中,对转基因智性本身和从事研发工作科学家(知识分子)的拒绝不可避免。一个吊诡的局面出现了:对于微观的生命科学、转基因技术,公众系统深入了解的意愿寥落,又不愿意相信研发者的专业意见,倒是愿意倾听人文学者的非专业表达。转基因是否安全,国际主流科学机构说的不算,谣言和谩骂更受欢迎。技术和产品不断被泼污水,各类阴谋论层处不穷,研发者被视为“汉奸”和“卖国贼”。反智让一切讨论的基础坍塌,剩下的只有情绪化的表达,支持者发声被围殴,谩骂者则英雄般凯旋。
饶毅认为:“对于转基因的最高分贝批评来自少数反智人士,他们不仅反对转基因本身,而且反对一切科学技术带来的进步。”(饶毅《转基因:警惕“投机”和“反智”》)高分贝的声音如果只是自我言说,毕竟影响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反智”对媒体的影响,只有通过媒体,分贝才能更进一步放大和扩散。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对11家主要报纸媒体19个月内转基因议题报道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发现媒体报道淡化科学、理性的学术色彩,弱化甚至省略科学基础的现象突出。在所选取的样本中,非科学知识类的报道有117篇,占比高达60.31%,而具备完整科学知识阐述的报道只有10.82%。
知识分子、科学家动辄得咎,民众失去了对真理和自然界探索的好奇心。反智的后果不只是影响了某一项科学技术的传播:2010年发布的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数据表明,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3.27%,在与2001年的欧盟15国、美日等国比较时发现,中国人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排名倒数第一。
一边是追求各种“吃哪补哪”、师法自然养生术热情高涨,一边是科学素养的极其低下,高低之间的落差,正是反智土壤培育的结果,转基因传播的障碍背后,是所有科学问题传播的迷局。
迷恋传统农业
在“天人合一”有机自然观和“反智”传统的影响下,社会对传统农业迷恋有着相当的市场,应用转基因技术的现代农业变得不可接受。有学者提出,传统农业是比工业化农业综合效益更高的生产方式。田松等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对工业文明进行批判和反省,需要从传统中汲取滋养。中国传统农学一直独步世界,早在工业文明起步之前,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技术。”
从农业的诞生、发展及现状看,质疑现代生物技术、希望重返传统农学,籍此回归自然无疑是矫枉过正。
农业从诞生之时起,选育品种、驯化家畜,无不以自然为对象,每一件事都是在改造自然。从文明诞生起,“天然”已经不存在了。农业诞生是人类第一次全球范围内进行基因改造。在距今13000年到3000年这一万年中,全球范围内至少有10个地方,人们针对特定的品种开始有选择的采集,再循小规模到大规模的翻耕,而后是灌溉和作物轮作,这其中包括中国人在8000年前左右进行的水稻选育和一系列耕作技术的总结。这些有意识的对植物基因的改造,使得人类文明看到了曙光,世界因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国是公认的世界栽培植物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但自然馈赠给我们的仍然远远不够。在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下,祖先们在驯化选育本地品种的同时,不得不从外域引进新品种。比如小麦,从西亚传入中国,历经数千年的反复艰难的栽培试验,最终在北宋以后代替谷子,成为北方人民的主粮。元代农书《农桑辑要》提倡在黄河流域引进和推广棉花、竺麻,明清时代又引进了玉米、土豆。正是像小麦、土豆、玉米这些“异乡客”,它们看起来一点也不本土、也不天然,却养活了中国人,缓解了人地紧张关系,推动了文明发展。
由于人地关系的紧张,中国传统农业最为讲究集约的土地利用、精耕细作和因地制宜,先民在改造利用各类低产田、战胜自然灾害等方面,有许多独特的智慧创造,该方式本身意味着对自然的改变。至迟到《农桑辑要》出现时,传统农学已经开始对唯风土论进行批判,该书对人的能动性有着充分的论述,能够改变农业生物的习性,使之适应新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讲,精耕细作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克服自然条件中的不利方面,利用其有利方面的一种巧妙的农艺。”比如,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在抗旱保墒实践中形成了耕-耙-涝-压-锄的耕作体系,动植物良种选育技术包括动物有性杂交等手段的应用也很早。
传统农业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有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那些醉心传统农业的观点,实则是人为割裂了农业发展的有机过程。一个问题是,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后,回归传统农业究竟该回到哪一个阶段?以人文最盛的江南为例:江南只到衣冠南渡后,到唐宋变为天下粮仓,在《禹贡》时代则是“厥土惟涂泥,厥田为下下”的景象。该地区低洼易涝,先民经过长期摸索,建立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塘埔灯田系统,经济面貌得以彻底改观。明清时代又出现堤塘生产方式:低洼地挖池,堆土为堤(或称为“基”),池中养鱼,堤上植桑,桑叶饲蚕,蚕矢饲鱼,池泥奎桑,循环利用,成为生态农业的雏形。满地涂泥、天下粮仓、桑塘田立体农业,这些渐进的过程都是传统的有机部分,回到哪一阶段才更符合热衷天然的人们对田园诗的想象?
按郑林等学者的观点,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对应,主要是为了反映农业发展的延续性、继承性。传统农业与以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农业之间,两者是承继发展而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农业技术的发展,有其自身演化规律。以育种技术为例,传统育种-杂交育种-生物技术育种,内在发展逻辑有其自我发育的内在机制和根据,又为社会需求推动。
从现实状况来看,中国古代科技,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验实践,都有一种趋于饱和的趋向,其中,传统农业技术在社会各项技术中的比重到明清时已降至很低的水平。在第一次绿色革命前,传统农业已经穷尽了可能。
1949年,中国人口5.4亿,到1987年,已经翻番达到了10.93亿(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年鉴)。这期间,粮食亩产则从68.62公斤增长了3.5倍,达到242.5公斤,人均占有粮食从不足210公斤增长到370公斤,增长了约1.8倍(亩产数据来自中国种植业信息网数据库,人均粮食产量则依据粮食总产和人口数量计算所得)。如果不是60年代至70年代矮化育种和杂交的优势利用,配合化学肥料、化学农药、灌溉技术、农业机械化等新技术的应用,灾难将很难避免。本世纪上半叶将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最为庞大的时期,人口总量将在2016年左右超过14亿,并且可能在2023—2047年期间一直保持在14.5亿的规模以上。如此庞大的人口,回归传统农业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么多人免于饥饿。
人类面临的难题不仅仅只有数以十亿计的人口,还有工业化导致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这其中也包括第一次绿色革命带来的弊端:化肥和农药投入的回报率已趋逐年下降,土壤肥力衰退,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的现象日益普遍等等。希望回归传统农业的学者们因此而百般责难现代农业技术:你们所承诺的进步,让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必须要明确的是,化肥、农药带来的后果,转基因可能对未来的影响,这些看起来超过人类预期的结果,其实并非完全“无意识”,它们恰恰包含在人类的意愿和选择中。那些负面的后果,很多是可以预见和可以避免的,只是人们没有选择而已。很难说某一项技术是邪恶或者正义的,技术被滥用或误用,不过是人类在放大自身的弱点。人类是否已经丧失了对技术本身的控制,这是一个涉及技术自主性的根本问题。在对待转基因技术上,也许我们该学习温纳(LangdonWinner),他在写《自主技术》时曾对技术控制的前景悲观,但后来,他仍然对技术的社会控制持乐观的态度。
要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生存难题,完全寄希望于从传统文化里寻找资源,恐怕只能是乌托邦。技术产生的问题还需要依靠技术来解决,对于农业领域来说,在穷尽了传统技术手段后,转基因等现代生物技术的产生,目的是解决日益尖锐的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等问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技术自身的内在需要。
结论与讨论
无论愿意不愿意,转基因讨论已经超越了实验室或者是特定的产业边界,成为了当前公共领域的一个部分。对“天人合一”有机自然观的误读,弥漫的反智氛围,对传统农业的迷恋,这些颇值得玩味的文化因素,深刻影响着该公共话题意义的生产与传播。
梳理有机自然观的发展脉络及对转基因传播的影响时,必须要看到的是,现代科学体系的诞生,得益于构造性自然观和受控实验的出现。所谓构造性自然观,是指基于假设和公理之上,运用逻辑导出推断,由此构建一个自洽有序的科学理论体系。构造性自然观具有可预见性和可证伪性,指导设计实验,又反过来接受实验结果的检验。而在今天,有机自然观和构造性自然观的冲突,不仅导致了转基因研发及传播面临诸多困难,而且正阻碍着中国产生新的科学创造。
不过,从科学史来看,也许不必要太在意转基因当前面临的传播障碍问题。到17世纪后半叶,西方科学革命理论准备已经基本完成,但直到18世纪,蒸汽机等技术革命才出现,之间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差,正是近代社会结构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之间不断调适的过程。在这约一百年时间里,西方完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准备,以及确立了将科学视为普遍概念的构造自然观。温纳在埃吕尔“技术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命令”,“技术是一系列的结构,技术的运行要求重新构建自己的环境。”由此得到的启示是,转基因技术要在国内被普遍接受,必须依赖两个条件,一是强大的社会经济结构即有强大的经济动力,一是该技术与国人普遍的自然观相结合。
在文化这堵厚墙面前,重构转基因所面临舆论环境的希望在于新的媒介和交流形式不断出现。最终影响讨论进程的,除了科学的进步外,还在于无形手的推动以及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选择。